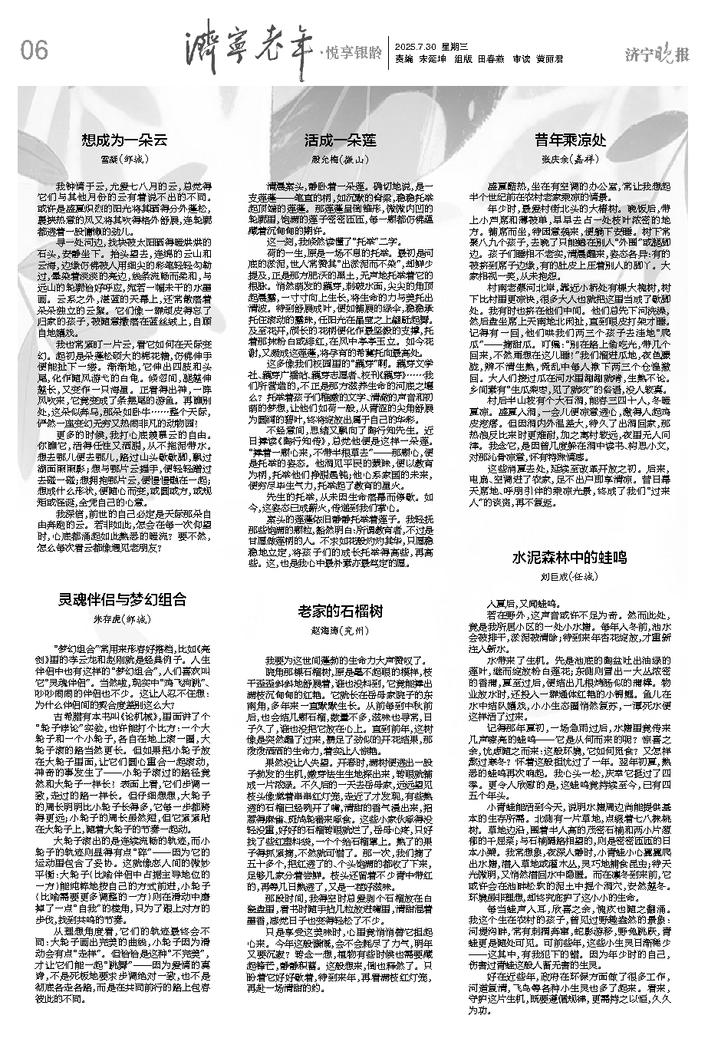张庆余(嘉祥)
盛夏酷热,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常让我想起半个世纪前在农村老家乘凉的情景。
年少时,最爱村街北头的大椿树。晚饭后,带上小芦席和薄被单,早早去占一处枝叶浓密的地方。铺席而坐,待困意袭来,便躺下安睡。树下常聚八九个孩子,去晚了只能蜷在别人“外围”或腿脚边。孩子们睡相不老实,清晨醒来,姿态各异:有的被挤到席子边缘,有的肚皮上压着别人的脚丫。大家相视一笑,从未抱怨。
村南老蔡河北岸,靠近小桥处有棵大槐树,树下比村里更凉快,很多大人也就把这里当成了歇脚处。我有时也挤在他们中间。他们总先下河洗澡,然后盘坐席上天南地北闲扯,直到眼皮打架才睡。记得有一回,他们哄我们两三个孩子去洼地“爬瓜”——摘甜瓜。叮嘱:“别在路上偷吃光,带几个回来,不然甭想在这儿睡!”我们溜进瓜地,夜色朦胧,辨不清生熟,慌乱中每人揪下两三个仓惶撤回。大人们接过瓜在河水里涮涮就啃,生熟不论。乡间素有“生瓜梨枣,见了就咬”的俗语,没人较真。
村后半山坡有个大石洞,能容三四十人,冬暖夏凉。盛夏入洞,一会儿便凉意透心,激得人起鸡皮疙瘩。但因洞内外温差大,待久了出洞回家,那热浪反比来时更难耐,加之离村较远,夜里无人问津。我念它,是因曾几度躲在洞中读书、构思小文,对那沁骨凉意,怀有特殊情感。
这些消夏去处,延续至改革开放之初。后来,电扇、空调进了农家,足不出户即享清凉。昔日幕天席地、呼朋引伴的乘凉光景,终成了我们“过来人”的谈资,再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