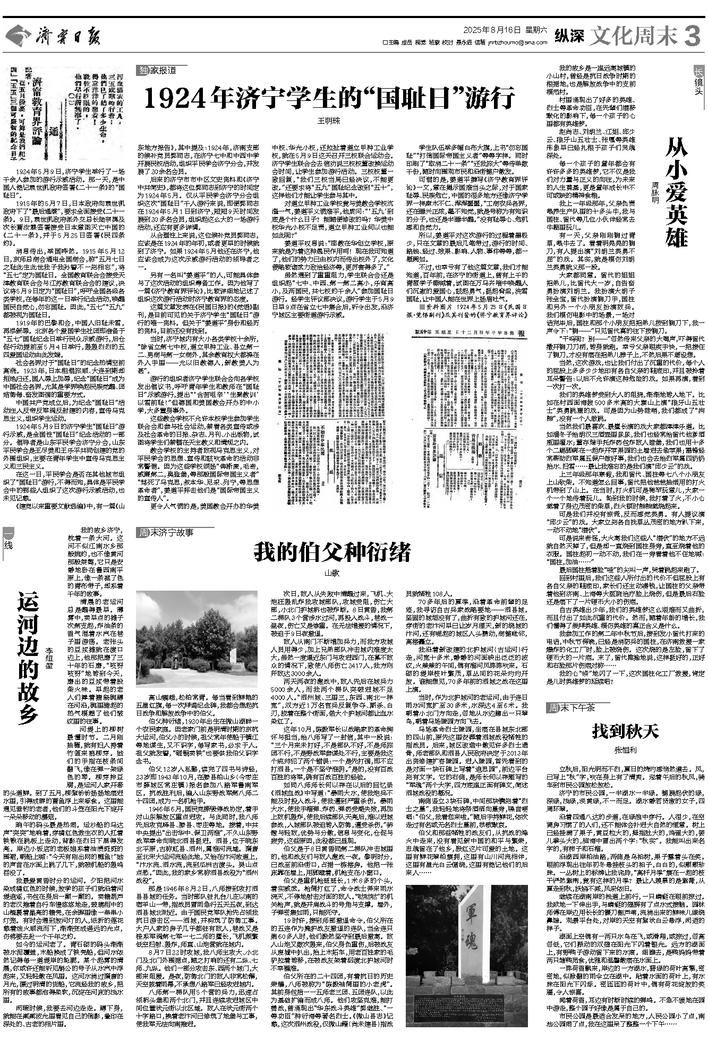我的故乡济宁,枕着一条大河。这河不似江南水乡那般婉约,也不像黄河那般桀骜,它只是安静地卧在鲁西南平原上,像一条褪了色的青布带子,却系着千年的故事。
清晨的老运河总是醒得最早。薄雾中,卖早点的摊子次第支起,炸油条的香气混着水汽在巷子里游荡。老张头的豆浆摊就在渡口边上,他那把磨了三十年的石磨,“吱呀吱呀”地转到今天,磨出的豆浆带着股柴火味。早起的老人们捧着搪瓷碗蹲在河沿,碗里腾起的热气模糊了他们皱纹里的往事。
河堤上的柳树最懂时节。二月刚抽穗,就有妇人挎着竹篮来掐柳芽。她们的手指在枝条间翻飞,像在弹一架绿色的琴。柳芽拌豆腐,是运河人家开春的头道鲜。到了五月,柳絮纷纷扬扬地落进水里,引得成群的曹鱼浮上来啄食。这里能遇见垂钓的老者,他们的斗笠在阳光下绽开一朵朵移动的蘑菇。
晌午的码头最是热闹。运沙船的马达声“突突”地响着,穿橘红色救生衣的人扛着铁锹在跳板上走动,背影在烈日下黑得发亮。岸边小饭店的老板娘系着油渍斑斑的围裙,朝船上喊:“今天有刚出网的鲤鱼!”她的声音在水面上跳了几下,就被机船的轰鸣吞没了。
我最爱黄昏时分的运河。夕阳把河水染成橘红色的时候,放学的孩子们就沿着河堤追逐,书包在身后一颠一颠的。卖糖葫芦的老汉推着自行车慢悠悠地走,玻璃柜中的山楂裹着晶亮的糖壳,在余晖里像一串串小灯笼。有时会遇到放河灯的人,纸折的莲花载着烛火顺流而下,渐渐变成遥远的光点,仿佛要去赴一个千年之约。
如今的运河老了。青石砌的码头渐渐被水泥覆盖,木船换成了铁壳船,但河水依然记得每一道堤岸的轮廓。某个起雾的清晨,你或许还能听见艄公的号子从水汽中浮起来,又轻轻散在风里。这河水淌过隋唐的月光,漂过明清的货船,它流经我的故乡,把所有的故事都泡得柔软,沉淀在河床的浅水里。
闲暇时候,我要去河边走走。蹲下身,就能在粼粼波光里看见自己的倒影,叠印在深处的、古老的相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