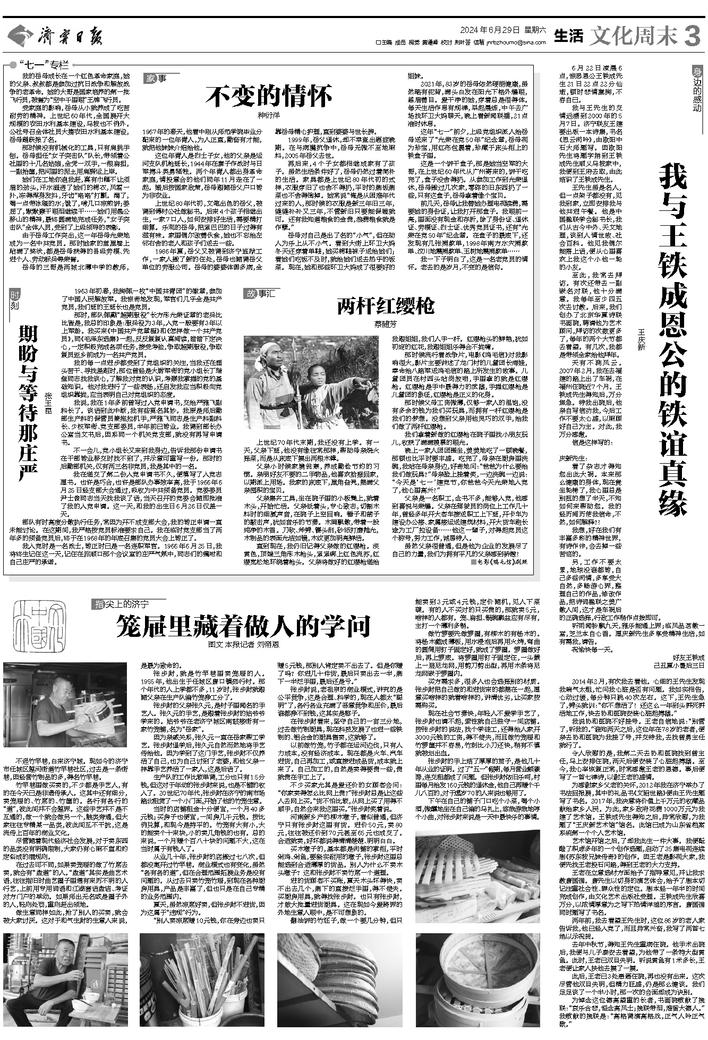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还没有上学。有一天,父亲下班,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帮助母亲烧火择菜,而是从床底下摸出两根木棒。
父亲小时候家境贫寒,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亲朋好友不要的二手物品,他喜欢拾掇回家,以期派上用场。我家的床底下,屋角旮旯,摆满父亲囤积的宝贝。
父亲集齐工具,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就着木头,开始忙活。父亲低着头,专心致志,切割木料时的细腻声音,在院子上空回响。锤子和凿子的敲击声,犹如音乐的节奏。木屑飘散,带着一股纯净的木香。刀砍、斧劈、镰头刮,砂纸打磨抛光,木制品的表面光洁如镜,木纹更加明亮鲜活。
直到现在,我仍旧记得父亲做的红缨枪。淡黄色,顶端三角形木枪头,紧紧绑上红色流苏,红缨宽松地环绕着枪头。父亲将做好的红缨枪递给我跟姐姐,我们人手一杆。红缨枪头的鲜艳,犹如初绽的红花,我跟姐姐乐得合不拢嘴。
那时候流行看战争片,电影《鸡毛信》对我影响很大,影片主要讲述了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路上所发生的故事。儿童团员在村西头站岗放哨,手里拿的就是红缨枪。红缨枪是手中最得力的武器,手握红缨枪是儿童团的象征,红缨枪是正义的化身。
那时候父母工资微薄,仅够一家人的温饱,没有多余的钱为我们买玩具,而拥有一杆红缨枪是我们的梦想。没想到父亲用他灵巧的双手,给我们做了两杆红缨枪。
我们拿着新做的红缨枪在院子里找小朋友玩儿,收获了满满羡慕的眼光。
晚上一家人团团围坐,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餐,那顿也比平时要丰盛。吃完了,母亲在厨房里洗碗,我站在母亲身边,好奇地问:“爸爸为什么要给我们做玩具?”母亲脸上挂着笑,一边洗碗一边说:“今天是‘七一’建党节,你爸爸今天光荣地入党了,他心里高兴!”
父亲是一名职工,念书不多,能够入党,他感到喜悦与荣耀。父亲在驾驶员的岗位上工作几十年,曾经多年开大客车接送职工上下班,开卡车为建设办公楼、家属楼运送建筑材料,开大货车跑长途为工厂拉设备……他这一辈子,对得起党员这个称号,努力工作,诚恳待人。
虽然父亲很普通,但是他为企业的发展尽了自己的力量,我们为拥有平凡的父亲感到骄傲!
■电影《鸡毛信》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