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回一趟南阳镇”,没其它理由,就因为它是故乡,是我人生记忆的一个原点,所以得去一趟。
近十来年大概回了两趟南阳。一次是几年前,三舅去世,我去奔丧。一次听说南阳镇被政府搞旅游开发,更名叫做南阳古镇,于是就回那里去看了一下,算是一次旅行。
这两次虽然心境不同,但得出的印象都是一样的,南阳变了。但究竟怎样变的,并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今天要好好去看看。
丁楼,是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离我现在的家大概有40公里,却成了离南阳最近的一个码头。驱车从滨河大道南行,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这里。果然,站在码头上向东望,南阳镇就在目力之内,看起来,比鱼台渡口码头要近很多。
丁楼码头修得很齐整,石头水泥砌成,有宽阔的停车场,方便旅行的人停靠车辆。临水的那一边修有台阶,渐漫的通向水里,也方便客人上下船只。临近几户人家,在庭院里经营起小饭馆的生意,专营微山湖炖鱼。不知道他的鱼炖的怎么样?但他家的那个院落位置却很别致,四方的宅院,东边和北边都朝向湖水,而且离湖水很近,触手可及的样子,也塑造了湖岸的样子。很让我回忆起,小时候生活在船上,打开后厫的小木门,将身子探出去,临水看鱼虾在水里游动的情景。


几只形制熟悉的小木船,湾在这家小饭馆的东边,在冬季的湖面上增添了几分静溢之美。四顾一下,没有看到渡船。遂向餐馆的老板询问?他给了我一个手机
号码,让我联系他,说20分钟就到,没想到服务还这么方便。
20分钟以后,船到了。许是近乡情怯,我的心竟然激动了一下,急忙走上船,坐在船主的旁边。
“应该是先向后倒船,向左边打舵,再向右边打舵,前进,就可以了。”这是我心里的默念,船主也照着默契。开船这活儿我还是比较熟悉。
心里痒、手也痒,想亲自开一下船,就与船主攀谈,说我老家是南阳的。他问我姓什么?我说姓赵。他又问,赵广业是谁?我说是我爷爷。哦!只有一个简单的“哦”,似是理解了很多。
我问:我能不能开一下船?船主没有吱声,却起身将驾驶座让给了我,用动作表达了意见。这就是南阳人,地方不大,都是亲戚,那一问一答就有了信任。再说,南阳的人谁不会开船呢?

行驶在浩渺的湖面上,看航道以外已经结了冰。此时的航道已经与过去不同。过去的航道是以水草和芦苇为界,现在装上了两排太阳能的航灯,即使船上没有探照灯,夜里也可以行船。前面几只孤鸭在水里游,我故意的加了一下油门,把发动机的声音弄得大了一点,惊得它们就飞了起来。高天云影下,很快就成了两个小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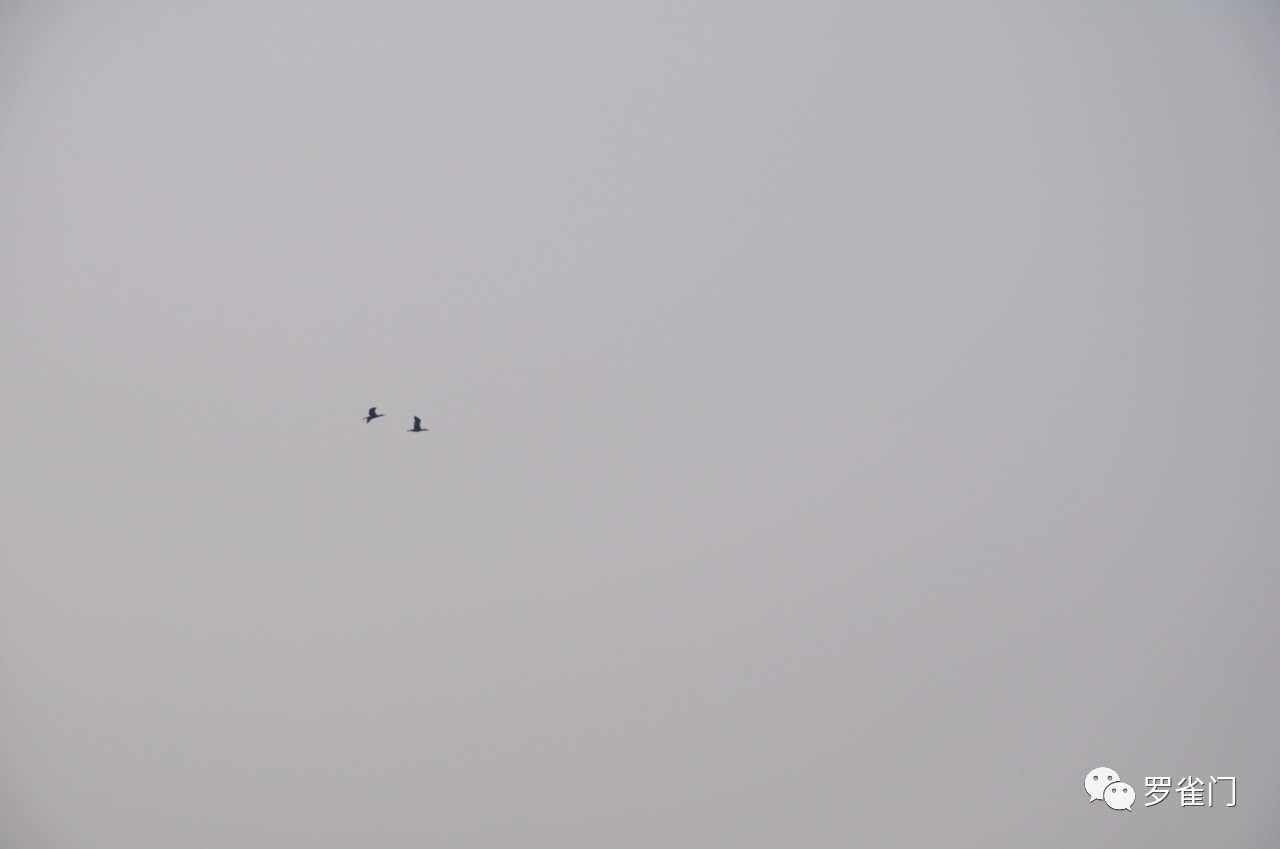
十几分钟以后船靠岸,大步跳到岸上,给船主告个别,熟悉似的向右一转,两只石狮子和一块介绍南阳古镇的旅游标志,让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过去的公社码头。向东就是南阳唯一的一条南北走向的长街了,当年吃螺蛳的地方就在那里。转过去,果然不错!
儿时的记忆虽然很浅,但因为单纯,却能在脑海里映得很深,我的很多儿时记忆都有这个特点。
政府是投了不少资,长长的石板街,已经全部更换成新石头了,比过去要平整很多,倒反而不如过去的有味。过去的石板路,有些高低不平,每一块石头凸起的地方,都因千百年的踩踏而变得锃亮,发着青色的光,下一场小雨,就变得温润如玉。
长街两旁的房子,也都翻建成古建筑的模样,弄一些招幌,卖一些当地的特产。与江南周庄那几处所谓的古镇无异。这是没有意义的做旧,我心里说。

特产还是不错的,红心鸭蛋,盐干鱼,都是南阳著名的特产,看到以后,咽窝里便多了一些口水。那红心鸭蛋,据长辈说,只有吃活食儿的鸭子生出的蛋,经过腌制才会有流着红油的心。微山湖的鸭子,都是放在湖里养的,每天在湖里哌哌呱的游着找食吃,不是小鱼虾就是螺师,岂不都是活食儿。至于那盐干鱼,很多人都以为是死掉的鱼腌的,其实不是。以前湖里的人打到鱼,首先会放到装着水的船舱里。然后再向过往的船只售卖,也留一些自吃。多余的部分,便杀了,及时的将小一些的鱼,铺在船头上晒。夏日湖面的太阳,象电烤箱,一切细菌不可能在此时滋生,两个小时就干了。对于那大一些的,便会加盐后,用绳子串起来晒,虽然需要的时间长一些,但因为盐的缘故。干了以后也很新鲜。这就是为什么小干鱼往往不咸,而大干鱼都是咸的一个原因。
一个小摊点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卖一种叫泥鸡的东西。记忆里,这种用泥烧出来的小鸡,是仿湖里的水鸡子做的。里而也要装一些水。用嘴一吹就发出“苏苏”的声响。两分钱一个,小时候很爱玩,没想到现在还有,只是不知道现在玩手机的孩子还爱几分。

好在做旧的房屋不算很多,走过一里多路,就没了。进入了有新有旧的区域。那新的就是南阳人近年建造的房屋,颜色、风格很随性,红砖青瓦或青砖红瓦都有。只有那旧一些的,才能基本保持青砖、青瓦长青苔的旧风貌,更让人觉得有点味。前面看到一排青色的瓦房,便离开大路走进去。没人,房子多己破败。每个木门都变得歪歪斜斜,有些已经朽掉了。院子里放着几根横着的大树,正不知何用时,走出一个人。冬天,头顶一个皮帽,戴一眼镜,手里拿一支铅笔。我立时明白,这是一个家具作坊。可他看我拿着相机,穿着休闲,却不知我是弄啥。

我递只烟,就有了攀谈,与前面的船主一样,他也知道我旧家的住处。这里是造船厂的宿舍,前面有个水道,就是下船的地方。啊!这个消息让我一惊,这就是过去的造船厂?小的时候,看着多大一片,现在怎么这样小了。他还告诉我,他是船厂的老木工,船厂倒闭了,工人都失了业。他就依靠原来的木工手艺,打一些小桌、小椅来卖。我看了他打好的一张香椿方桌和一个正在制作的椅子。果然纯手工,没有一颗钉子,全是榫结构。样子、做工都也精细,带着一点古朴的美。他姓黄,我们互留了手机号码,暂不知为啥,就留了。可能在我,是有几分怀旧的念想,但是在他,却可能是一份多卖两张桌子的希冀。
“只我这一辈儿了,下面的孩子们都不学,我不干就失传了!”这是告别时黄木匠说的话,不像在告别我,倒像在告别一个时代。

我知道从这里再往前走,不远就快到北堤了!这一段的记忆应该是出现很多的土胚房。上面苫着苇草,算作是瓦。同样也是泥挑的墙院中,常有几棵支棱的枣树。徜是冬天,就有几只乌溜的鸟雀蹲在树上,是麻雀、乌鸦还是其它不知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南阳种那么多枣树?几乎家家都有,我大舅家的门口也有一棵。倘若季节对了,就能用长长的竹篙捅一下,弄下几只来吃。或许也会留下一只,枣肉从中间环切一下,再吃掉一半,用两根苇篾插上去。苇篾的两端粘上两个泥团以平衡。倒过来,枣核的尖向下,放到桌上。用手一拨,也不倒,颤巍巍的转,也有很大的乐趣。
倘或夕阳斜照在枣树间,有晾晒的渔网,光影便很有可能透过网眼,稀稀落落的打在补网的姑娘身上。那是南阳的姑娘,带着些枣树的质朴,也有一些荷花般灵动的姑娘......
近了,近了,离心中的家近了。
远了,远了,离那个时代远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