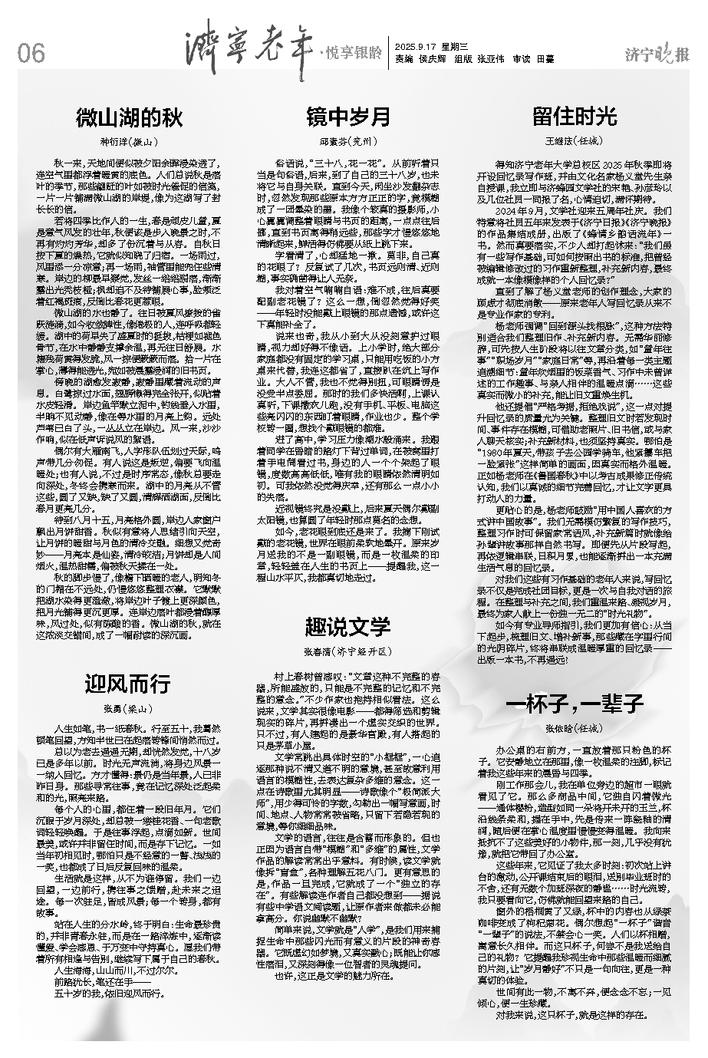张春清(济宁经开区)
村上春树曾感叹:“文章这种不完整的容器,所能盛放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不少作家也抱持相似看法。这么说来,文学其实很像电影——都得筛选和剪辑现实的碎片,再拼凑出一个虚实交织的世界。只不过,有人建起的是豪华宫殿,有人搭起的只是茅草小屋。
文学常跳出具体时空的“小框框”,一心追逐那种说不清又道不明的意境,甚至故意利用语言的模糊性,去表达复杂多维的意念。这一点在诗歌里尤其明显——诗歌像个“极简派大师”,用少得可怜的字数,勾勒出一幅写意画,时间、地点、人物常常被省略,只留下若隐若现的意境,等你细细品味。
文学的语言,往往是含蓄而形象的。但也正因为语言自带“模糊”和“多维”的属性,文学作品的解读常常出乎意料。有时候,读文学就像拆“盲盒”,各种理解五花八门。更有意思的是,作品一旦完成,它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存在”。有些解读连作者自己都没想到——据说有些中学语文阅读题,让原作者来做都未必能拿高分。你说幽默不幽默?
简单来说,文学就是“人学”,是我们用来捕捉生命中那些闪光而有意义的片段的神奇容器。它既虚幻如梦境,又真实戳心;既能让你感性落泪,又深刻得像一位智者的灵魂提问。
也许,这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