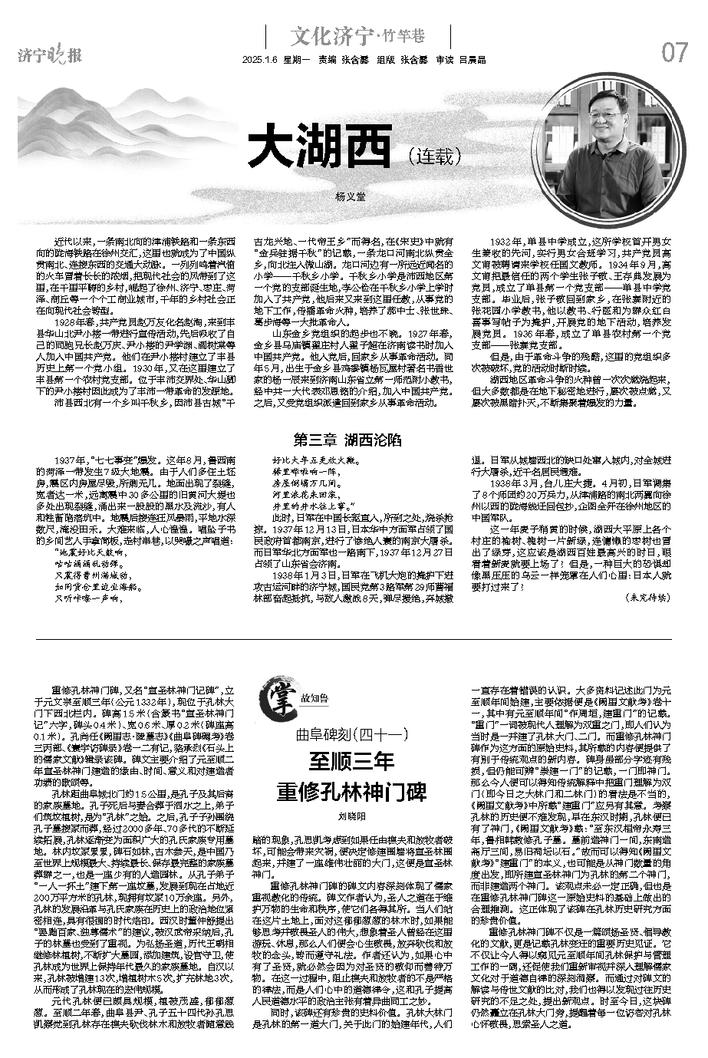刘晓阳
重修孔林神门碑,又名“宣圣林神门记碑”,立于元文宗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现位于孔林大门下西北栏内。碑高1.5米(含篆书“宣圣林神门记”六字,碑头0.4米)、宽0.6米、厚0.2米(碑座高0.1米)。孔尚任《阙里志·陵墓志》《曲阜碑碣考》卷三丙部、《寰宇访碑录》卷一二有记,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辑录该碑。碑文主要介绍了元至顺二年宣圣林神门建造的缘由、时间、意义和对建造者功绩的歌颂等。
孔林距曲阜城北门约1.5公里,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孔子死后与妻合葬于泗水之上,弟子们筑坟植树,是为“孔林”之始。之后,孔子子孙围绕孔子墓接冢而葬,经过2000多年、70多代的不断延续拓展,孔林逐渐变为面积广大的孔氏家族专用墓地。林内坟冢累累,碑石如林,古木参天,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墓葬群之一,也是一座少有的人造园林。从孔子弟子“一人一抔土”建下第一座坟墓,发展到现在占地近200万平方米的孔林,现拥有坟冢10万余座。另外,孔林的发展沿革与孔氏家族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时代烙印。西汉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后,孔子的林墓也受到了重视。为弘扬圣道,历代王朝相继修林植树,不断扩大墓园,添加建筑,设官守卫,使孔林成为世界上保持年代最久的家族墓地。自汉以来,孔林被增建13次,增植树木5次,扩充林地3次,从而形成了孔林现在的宏伟规模。
元代孔林便已颇具规模,植被茂盛,郁郁葱葱。至顺二年春,曲阜县尹、孔子五十四代孙孔思凯察觉到孔林存在樵夫砍伐林木和放牧者随意践踏的现象,孔思凯考虑到如果任由樵夫和放牧者破坏,可能会带来灾祸,便决定修建围墙将宣圣林围起来,并建了一座雄伟壮丽的大门,这便是宣圣林神门。
重修孔林神门碑的碑文内容深刻体现了儒家重视教化的传统。碑文作者认为,圣人之道在于维护万物的生命和秩序,使它们各得其所。当人们站在这片土地上,面对这郁郁葱葱的林木时,如果能够思考并敬畏圣人的伟大,想象着圣人曾经在这里游玩、休息,那么人们便会心生敬畏,放弃砍伐和放牧的念头,转而遵守礼法。作者还认为,如果心中有了圣贤,就必然会因为对圣贤的敬仰而善待万物。在这一过程中,阻止樵夫和放牧者的不是严格的律法,而是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这和孔子提高人民道德水平的政治主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同时,该碑还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孔林大林门是孔林的第一道大门,关于此门的始建年代,人们一直存在着错误的认识。大多资料记述此门为元至顺年间始建,主要依据便是《阙里文献考》卷十一,其中有元至顺年间“作周垣,建重门”的记载。“重门”一词被现代人理解为双重之门,即人们认为当时是一并建了孔林大门、二门。而重修孔林神门碑作为这方面的原始史料,其所载的内容便提供了有别于传统观点的新内容。碑身虽部分字迹有残损,但仍能可辨“崇建一门”的记载,一门即神门。那么今人便可以得知传统解释中把重门理解为双门(即今日之大林门和二林门)的看法是不当的,《阙里文献考》中所载“建重门”应另有其意。考察孔林的历史便不难发现,早在东汉时期,孔林便已有了神门,《阙里文献考》载:“至东汉桓帝永寿三年,鲁相韩敕修孔子墓。墓前造神门一间,东南造斋厅三间,易旧祠坛以石。”故而可以得知《阙里文献考》“建重门”的本义,也可能是从神门数量的角度出发,即所建宣圣林神门为孔林的第二个神门,而非建造两个神门。该观点未必一定正确,但也是在重修孔林神门碑这一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做出的合理推测。这正体现了该碑在孔林历史研究方面的珍贵价值。
重修孔林神门碑不仅是一篇颂扬圣贤、倡导教化的文献,更是记载孔林变迁的重要历史见证。它不仅让今人得以窥见元至顺年间孔林保护与管理工作的一隅,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并深入理解儒家文化对于道德自律的深刻洞察。而通过对碑文的解读与传世文献的比对,我们也得以发现过往历史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新观点。时至今日,这块碑仍然矗立在孔林大门旁,提醒着每一位访客对孔林心怀敬畏,思索圣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