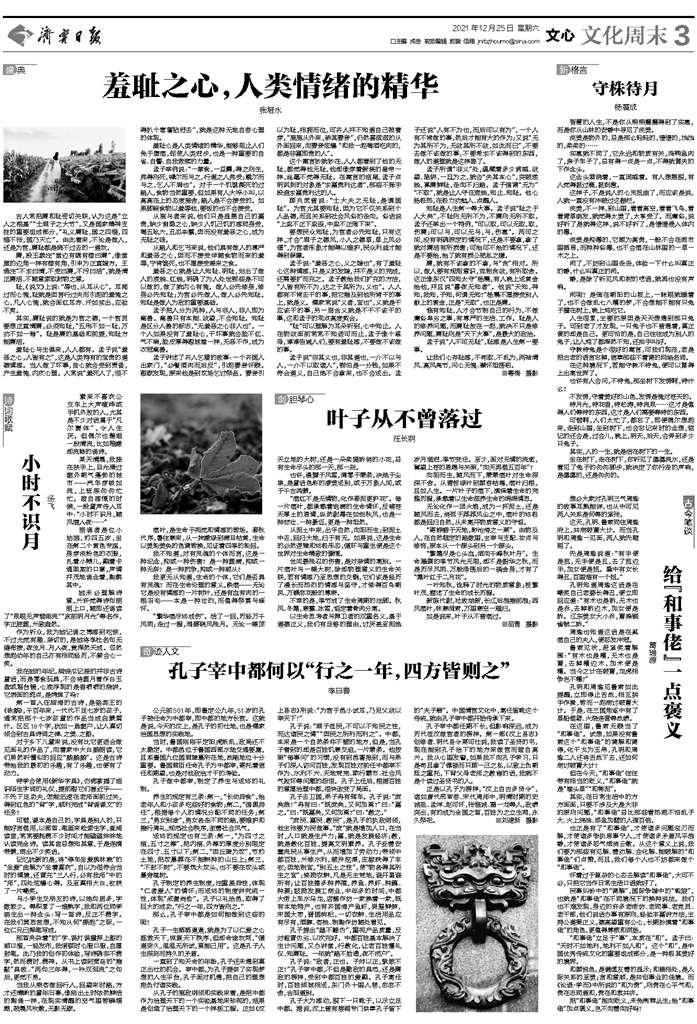素来不喜欢公交车上大声喧哗或手机外放的人,尤其是不少对话属于“凡尔赛体”,令人生厌。但偶尔也邂逅一股清流,比如稚嫩却流畅的诵诗。
某天清晨,我挂在扶手上,目光滑过窗外朝气蓬勃的城市——汽车穿梭如流,上班族匆匆忙忙。暗自感慨的时候,一段童声传入耳中:“小时不识月,随风潜入夜……”
朗诵者是位小姑娘,约四五岁,坐在第二个黄色专座,身穿淡粉色的衣服,扎着小辫儿,戴着卡通图案的口罩,声情并茂地诵念着,陶醉其中。
她未必理解诗意,兴许觉得诗句朗朗上口,随即还诵读了“泉眼无声惜细流”“床前明月光”等名作,字正腔圆,兴致盎然。
作为听众,我为她记诵之博感到吃惊,不过尤觉有趣、亲切的,是她将李杜名句无缝衔接,夜生月、月入夜,竟浑然天成。忽然想起幼年的自己亦有相同经历,不禁会心一笑。
我在她的年纪,脑袋瓜记挂的并非古诗童话,而是零食玩具,不会将圆月看作白玉盘或瑶台镜,心底浮现的是香喷喷的烧饼。它表面的斑点,是烤焦了吗?
第一首入住脑海的古诗,是骆宾王的《咏鹅》,千百年来,一代代不足七岁的孩子,通常把那个七岁孩童的作品当成启蒙篇什。区区18个字,犹如一扇窗户,让人真切领会到古典诗词之律、之美、之韵。
对于乡下儿童来说,没有比它更适合做见面礼的作品了,向着家中大白鹅朗读,它们果然听懂似的回应“鹅鹅鹅”。这是古诗带给我的最初的乐趣,有了乐趣,也便有了动力。
待学会使用《新华字典》,仿佛掌握了结识陌生字词的礼仪,提前跟它们套近乎——不先下足功夫,怎能迅速在老师面前过关,得到红色的“背”字,顺利完成“背诵课文”的任务?
可惜,课本是自己的,字典是别人的,只能好言借用,以部首、笔画来检索生字,查阅读音,常常要耗费不少时间才能磕磕绊绊地认读完全诗。读其音总想知其意,于是连猜带蒙,闹出不少笑话。
记忆犹新的是,将“停车坐爱枫林晚”的“坐爱”曲解为“坐着喜欢”,自以为很符合当时的情境,还冒充“三人行,必有我师”中的“师”,四处炫耀心得。及至真相大白,收获了一片嘲笑。
与小学生交朋友的诗,以绝句居多,字数较少。等积累了一堆熟字,我和两位同学萌生出一种念头:写一首诗,反正不费字。在我们冥思苦想,不知从何“撕起”之际,一位仁兄已挥笔写成。
那首夹杂着“的”字、误打误撞押上韵的顺口溜,一经发布,我俩顿时心服口服,自愿封笔。此乃我的创作初体验,写诗确实不费字,然而费时、费神。从书上读到贾岛的“推敲”典故、“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之句后,更觉不易。
当我从乘客做回行人,回望来时路,方才还清晰的童年旧事,像刚出土时依然鲜活的陶俑一样,在现实清醒的空气里转瞬模糊,被晨风吹散,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