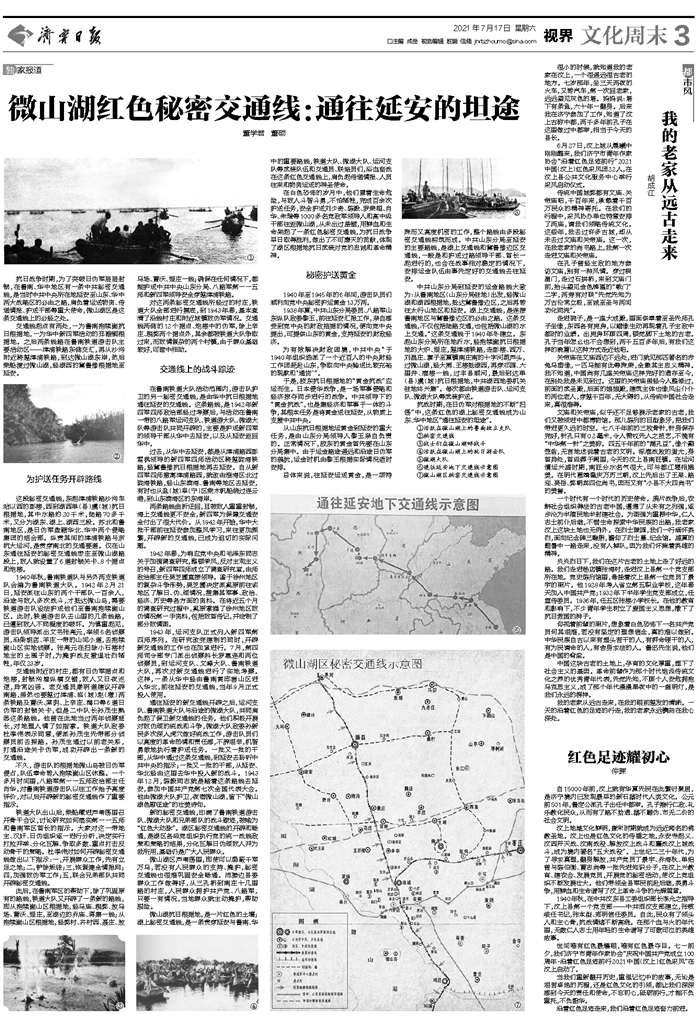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的老家在汶上,一个很遥远很古老的地方。七岁那年,坐三天两夜的火车,又转汽车,第一次回老家,远远望见灰色的塔。妈妈说:塔下有条鱼,六十年一翻身。后来我在济宁参加了工作,知道了汶上古称中都,两千多年前孔子在这里做过中都宰,相当于今天的县长。
6月27日,汶上城从晨曦中刚刚醒来,我们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沿着红色足迹前行”2021中国(汶上)红色采风团22人,在汶上县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举行采风启动仪式。
传统中国城郭都有文庙、关帝庙吧,千百年来,承载着千百万民众的精神寄托。在我们的行程中,采风协办单位特意安排了两庙,请我们领略传统文化。这些年,我去过许多古城,却从未去过文庙和关帝庙。这一次,在我老家的尚书路上,我第一次走进文庙和关帝庙。
在孔子曾经主政的地方参访文庙,别有一种风情。穿过棂星门,走过石拱桥,来到文庙门前,抬头望见金色牌匾的“戟门”二字,两旁有对联“先觉先知为万古伦常立极,至诚至圣与两间功化同流”。
走进院子,是一座大成殿,里面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坐像,东西各有庑房,以蜡像生动再现着孔子主政中都时的业绩。出庑房环顾四周,顿觉脚下土地的古老。孔子当年怎么也不会想到,两千五百多年后,有我们这样的晚曹以这种方式走近他吧。
关帝庙在文庙西边不远处,进门就见那匹著名的赤兔马塑像,一匹马能有此等殊荣,全赖其主忠义精神。我不知道,中国尚有几座关帝庙这样完好的遗存至今,在别处我是未见到过。这里的关帝庙虽经今人整修过,前面的武圣殿,后面的娘娘殿,建筑主体也像风尘仆仆的两位老人,穿越千百年,无大碍的,从传统中国社会走来,真很难得。
文庙和关帝庙,似乎还不足够展示老家的古老,我们又被领进中都博物馆。那儿陈列的巨型象牙,把我们带进更久远的时空。七八千年前的三枚骨针,针身保存完好,针孔只有0.2毫米,令人赞叹先人之技艺,不愧有“中华第一针”之美称。四五千年前的“漏孔豆”,像个戴笠翁,无言地述说着古老的文明。涿鹿战败的蚩尤,身首异处,首级葬于阙里,今天的汶上县南旺镇。在运河漕运兴盛时期,南旺分水名气很大,可与都江堰相媲美。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汶上先后出了王杲、路迎、吴岳、郭朝宾四位尚书,因而又有“小县不大四尚书”的美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鸦片战争后,农耕社会组织得法的古老中国,遭遇了从未有之列强,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图强为重振中华,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不惜生命探索中华民族的出路,我老家汶上这块土地也无例外。在烈士陵园,我们一行缅怀英烈,面向纪念碑三鞠躬,瞻仰了烈士墓、纪念馆。盛夏的酷暑中一路走来,没有人掉队,因为我们怀揣着英雄的精神。
炎炎烈日下,我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走了好远的路。我们走进杨店镇张海村,走进汶上县第一个党支部所在地。党史陈列馆里,悬挂着汶上县第一位党员丁景宇的照片。他1928年考入省立第五职业学校,这年春天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下半年学生党支部成立,任宣传委员。1936年,任五区张楼小学校长。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不少青年学生树立了爱国主义思想,撒下了抗日救国的种子。
仰视着前辈的照片,想象着白色恐怖下一名共产党员何其艰难,若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真的难以做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先生说,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的文化厚重,埋下了社会主义的基因。革命前辈作为那个时代饱汲传统文化之养的优秀青年代表,先觉先知,不顾个人安危拥抱马克思主义,成了那个年代漫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我的老家从远古走来,在我的眼前越发的清晰。一天的沿着红色的足迹的行走,我的老家永远镌刻在我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