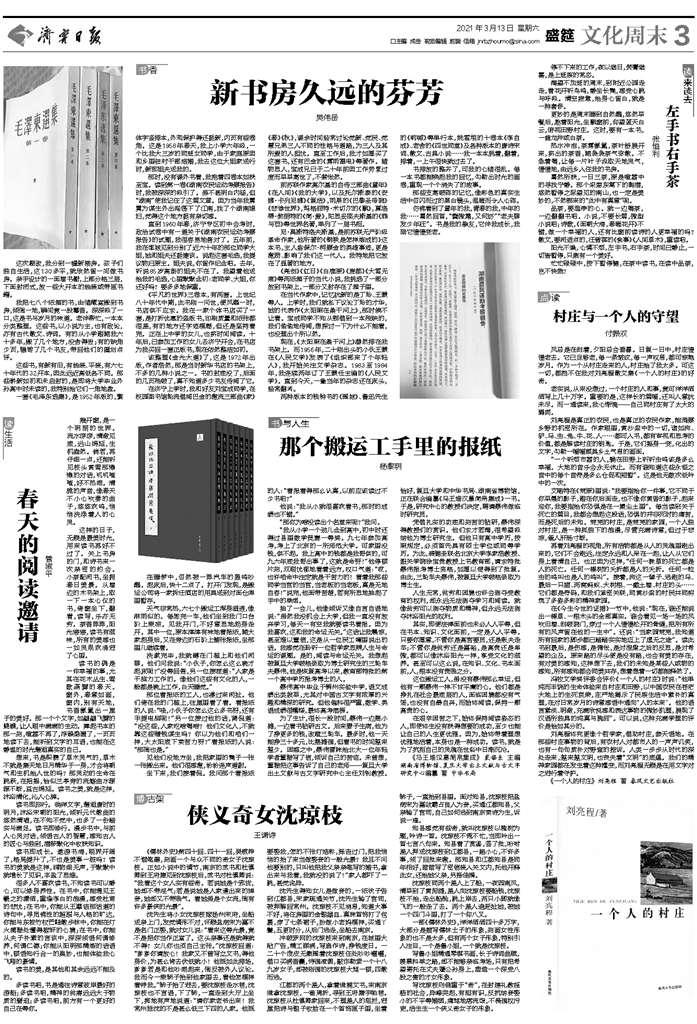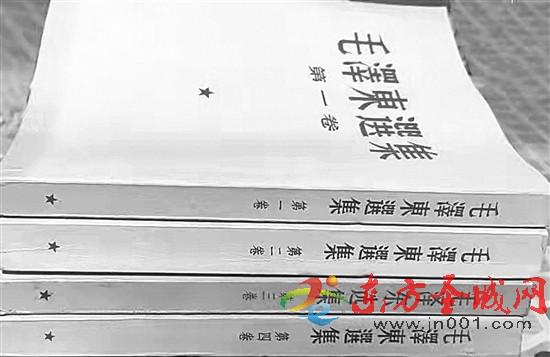这次棚改,我分到一幢新楼房。孩子们独自生活,这130多平,就欣然留一间做书房。亲手设计的一面墙书橱,上部分格三层,下面封闭式,放一些大开本的线装或带匣书籍。
我把七八个纸箱的书,由储藏室搬到书房,倾倒一地,瞬间竟一股霉香。深深吸了一口,这是书与岁月的味道。老伴帮忙,一本本分类整理。这些书,以小说为主,也有政论,亦有古代散文、诗词。有的从小学跟随我六十多年,搬了几个地方,没舍得丢;有的缺角少页,辗转了几个书友,带回他们的圈划点评。
这些书,有新有旧,有线装、平装,有六七十年代的32开本,因此远近高低各不同。那些崭新如初和未启封的,是即将大学毕业外孙高中时未读的,我特别给它们一角地盘。
一套《毛泽东选集》,是1952年版的,繁体字竖排本,外观保护得还挺新,内页有些卷角。这是1958年春天,我上小学六年级,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同班女同学,由于家庭原因和乡里驻村干部结婚,我去这位大姐家送行时,新郎姐夫送我的。
那时,没有课外书看,我抱着四卷本如获至宝。读到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我被深深的吸引了。虽不甚明白内涵,但“湖南”使我记住了这篇文章。因为当年我舅舅为谋生外出闯荡下了江南,找了个湖南媳妇,觉得这个地方挺有亲切感。
直到1960年春,济宁专区初中会考时,政治试卷中有一道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试题,我很容易地答对了。五年前,我在邹城见到分别了近六十年的那位同学大姐,她和姐夫还挺健谈。说起这套毛选,我提议物归原主。姐夫说,你留作纪念吧。去年,听说85岁高龄的姐夫不在了。我望着他送给我的毛选,心里默默念叨:老同学、大姐,你还好吗?要多多地保重。
《平凡的世界》三卷本,有两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此书刚一问世,便风靡一时,书店供不应求。我在一家个体书店买了一套,是打折优惠的盗版书,印刷质量和纸张都很差,有的地方还字迹模糊,但还是坚持看完。正在上中学的女儿,也挤时间阅读。十年后,已参加工作的女儿去济宁开会,在书店为我买回一套正版书,现在依然整洁如初。
该整理《金光大道》了,这是1972年出版,作者浩然,那是当时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不多的几种小说之一。书的封底没了,后面的几页残破了,真不知道多少书友传阅了它。
在济宁上学时,我和好友刘宝成同学,在校园图书馆轮流借阅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课余时间经常讨论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性格与道路,为三人及其所爱的人担忧。直至工作后,我才如愿买了这套书,还有巴金的《雾雨雷电》等著作。睹物思人,宝成兄已于二十年前因工作劳累过度而早早离世了,不禁怅然。
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以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世界名著,单列了一层书柜。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前苏联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他所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主人翁保尔·柯察金的英雄事迹,更是激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我特地把它放在了显著的地方。
《亮剑》《红日》《白鹿原》《废都》《大雪无痕》等两纸箱子的当代小说,我挑选了一部分放到书架上,一部分又封存在了箱子里。
在当代作家中,记忆犹新的是丁玲、王蒙等人。上学时,我们就私下议论丁玲的才华,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时候不让看。宝成同学不知从哪借到一本残缺的,我们偷偷地传阅,想探讨一下为什么不能看,也没理出个所以然。
现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赫然排在我书架上。而1956年,二十刚出头的小伙王蒙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开始关注文学杂志。1983至1984年,我连续两年订了王蒙任主编的《人民文学》。直到今天,一叠当年的杂志还在床头,经常翻阅。
两种版本的钱钟书的《围城》、鲁迅先生的《呐喊》等单行本,姚雪垠的十卷本《李自成》、老舍的《四世同堂》及各种版本的唐诗宋词、散文、古典小说……我一本本挑着,翻着,排着,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书排放的整齐了,可我的心绪很乱。每一本书都能唤起我的回忆,勾勒出时光的画卷,重现一个个消失了的故事。
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像彩色的真实生活中忽闪而过的黑白镜头,温暖而令人心碎。
仿佛看到了童年的我,青春的我,中年的我……蓦然回首,“鬓微霜,又何妨”“老夫聊发少年狂”。书是我的挚友,它伴我成长,我陪它慢慢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