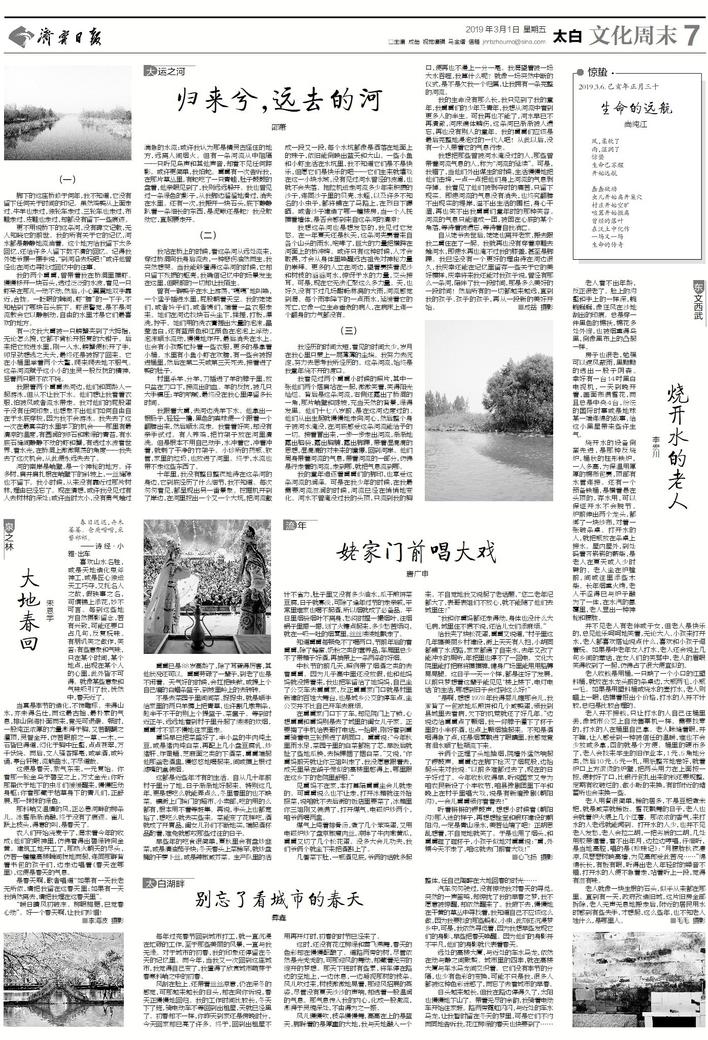老人看不出年龄,反正很老了。脸上的沟壑和手上的一样深,蜿蜿蜒蜒,像狂风在沙地刮出的印痕。总是穿一件黑色的棉袄,棉花多处外绽,也被烟熏得乌黑,倒像黑布上的凸起一样。
房子也很老,勉强可以遮风蔽雨,黑黝黝的透出一股子阴森。幸好有一台14吋黑白电视机,一天到晚开着,画面布满雪花,而且总是中央4台,纷纭的国际时事或是地球某一端连绵的战事,给这小黑屋带来些许生气。
烧开水的设备倒蛮先进,是那种反烧炉,桶状的柱形铁炉,一人多高,为保温用厚厚的棉布包裹,顶部有水管连接。还有一个预备铁桶,是横着悬在头顶的,存水用,可以保证开水不会脱节。炉前伸出两个龙头,都绑了一块纱布,对着一张破条桌。打开水的人,就把瓶放在条桌上接水。屋内屋外,到处码着齐崭崭的薪柴,是老人在夏天或人少时劈的。老人坐在炉膛前,间或往里添些木柴。长年烟熏火烤,老人干涩得已与炉子融为了一体,在水汽的氤霭里,老人显出一种神秘和朦胧。
并不见老人有老伴或子女,但老人是快乐的,总见他乐呵呵地笑着,无论大人、小孩来打开水,老人都喜欢搭讪说点什么,喜欢和小孩子逗着玩。如果是中老年女人打水,老人还会说上几句乡间的荤话,在女人们的笑骂中,老人的眉眼笑得收到了一起,仿佛占了很大便宜似的。
老人收钱是用桶,一只缺了一个小口的红塑料桶,就放在水龙头前的条桌边,大瓶两毛,小瓶一毛。如果是用塑料桶或烧水的壶打水,老人则瞄上一眼,估摸着报出个价格,打水的人并不计较,总归是比较合理的。
老人并不接钱,只让打水的人自己往桶里丢,像城市公交上自动售票机一样。需要找零的,打水的人在桶里自己拿。老人眯缝着眼,并不瞧,让人感受到一种被信任的温暖,谁也不会少放或多拿,图的就是个方便。桶里的硬币多了,老人会找来学生的旧作业本,1元、5角地分类,然后10元、5元一札,用纸整齐地卷好,就着炉口上方滚烫的炉壁,把两头用力在上面按一按,便封好了口,比银行包扎出来的钱还要规整,定期有收破烂的、做小贩的来换,有时附近的储蓄所也会来换一些。
老人用餐很简单,稀的居多,不是豆粑煮米粑,就是咸菜就稀饭。雪花飘舞的日子,老人也会就着炉火煨上几个红薯。那浓浓的香气,来打水的人老远就能闻到。打开水的人少,也并不见老人发愁,老人会拉二胡,一把劣质的二胡,几处用胶带缠着,看不出年月,边拉边哼唱,仔细听,是当地高腔,唱的是《珍珠记》:“月朦胧秋夜凄凉,风瑟瑟树映高墙,为见高郎受此苦况……”绵绵长长,有板有眼,听得出老人年轻时的嗓音不错,打开水的人便不急着走,站着听上一段,觉得有滋有味。
老人就像一块生根的石头,似乎从来都在那里。直到有一天,政府改造旧城,这片旧房全部拆除,老人无声无息地搬走后,附近的居民用水时感到有些失手,才想起,这么些年,也不知老人姓什么,是哪里人。■毛毛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