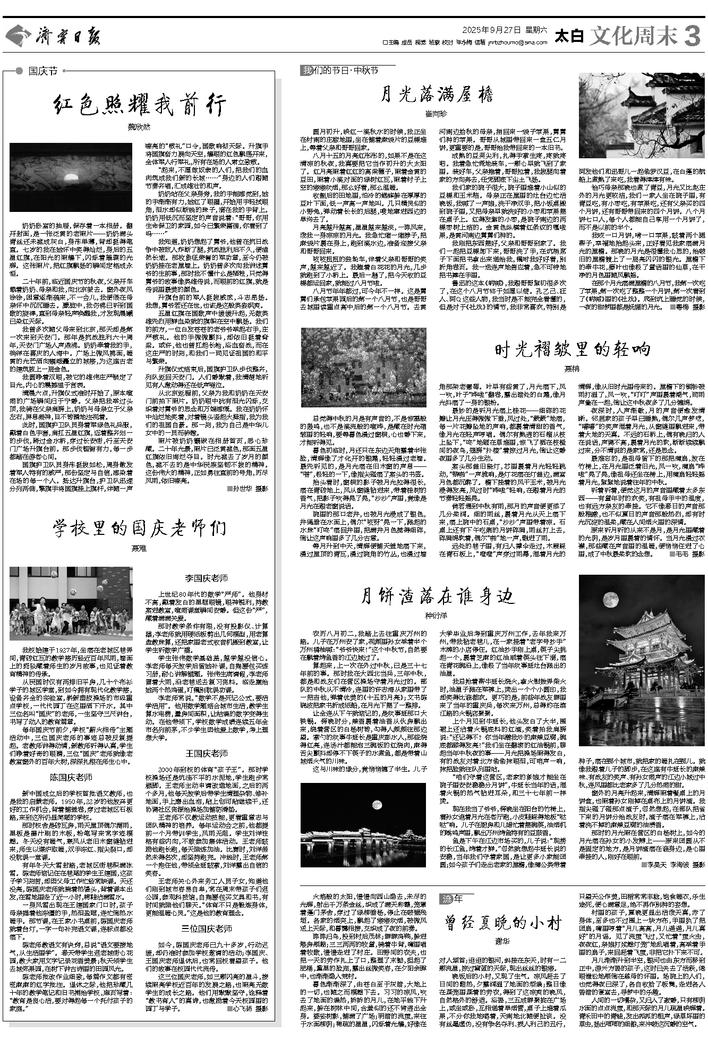农历八月初二,我踏上去往重庆万州的路。儿子在万州安了家,视频里孙女举着半个万州橘柚喊:“爷爷快来!”这个中秋节,自然要在飘着烤鱼香的江边城过了。
算起来,上一次在外过中秋,已是三十七年前的事。那时我在大西北当兵,三年中秋,都是和战友们在营区操场守着月光过的。部队的中秋从不清冷,连里的许志海从家里带了一把吉他,弹着优美的《十五的月亮》;文书陈晓波把家书折成纸船,在月光下摆了一整排。
让全连从下午就惦记的,是炊事班那口大铁锅。傍晚时分,辣香裹着油香从伙房飘出来,绕着营区的白杨树转,勾得人频频往那边望。掌勺的炊事牛班长是重庆彭水人,那些烧得红亮,连汤汁都能泡三碗饭的红烧肉,麻得舌尖颤抖却停不下筷子的水煮鱼,都是带着山城烟火气的川味。
这与川味的缘分,竟悄悄缠了半生。儿子大学毕业后考到重庆万州工作,去年我来万州,带我钻老巷儿,在一家挂着“老字号抄手”木牌的小店停住。红油抄手刚上桌,筷子尖挑起一个,裹着芝麻的红油顺着筷头往下滴,落在青花碗沿上,像极了当年炊事班灶台溅出的油星。
我总抢着帮牛班长烧火,拿火钳拨弄柴火时,油星子溅在军裤上,烫出一个个小圆印,我却笑得比谁都欢。更巧的是,前些年战友群里来了当年的重庆兵,每次来万州,总得约在滨江路的火锅店聚聚。
上个月见到牛班长,他头发白了大半,围裙上还沾着火锅底料的红渣,笑着拍我肩膀说:“还记得不?你当年蹭我炒的麻辣豆腐,碗底都舔得发亮!”我们坐在翻滚的红油锅前,聊起当年中秋夜的事——月光把操场照得发白,有的战友对着北方偷偷抹眼泪,可哨声一响,抹把脸就往队列里站。
“咱们守着这营区,老家的爹娘才能坐在院子里安安稳稳分月饼”,牛班长当年的话,混着火锅的热气钻进耳朵,和三十七年前一样烫。
现在我当了爷爷,傍晚坐在阳台的竹椅上,看孙女追着月光在客厅跑,小皮鞋踩得地板“哒哒”响。儿子在厨房和儿媳忙着摆碗筷,油烟机的嗡鸣声里,飘出万州烤鱼特有的豆豉香。
鱼是下午在江边市场买的,儿子说:“现捞的长江鱼,烤着才鲜。”忽然就想起牛班长说的安稳,当年我们守着家国,是让更多小家能团圆;如今孩子们走出老家的屋檐,像蒲公英带着种子,落在哪个城市,就把家的暖扎在哪儿。就像我跟着儿子的脚步,在这座有牛班长的麻辣味、有战友的笑声、有孙女闹声的江边小城过中秋,连风里都比老家多了几分热闹的甜。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清辉照着餐桌上的月饼盒,也照着孙女刚掉在桌布上的月饼渣。我指尖碰了碰那点渣子,忽然想起,在部队把省下来的月饼分给战友时,渣子落在军裤上,沾着洗不掉的麻辣豆腐的油渍香。
那时的月光照在营区的白杨树上,如今的月光落在孙女的小发辫上——原来团圆从不是固定的地方,是月饼渣落在谁身边,是心里牵挂的人,刚好在眼前。
■李昊天 李海波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