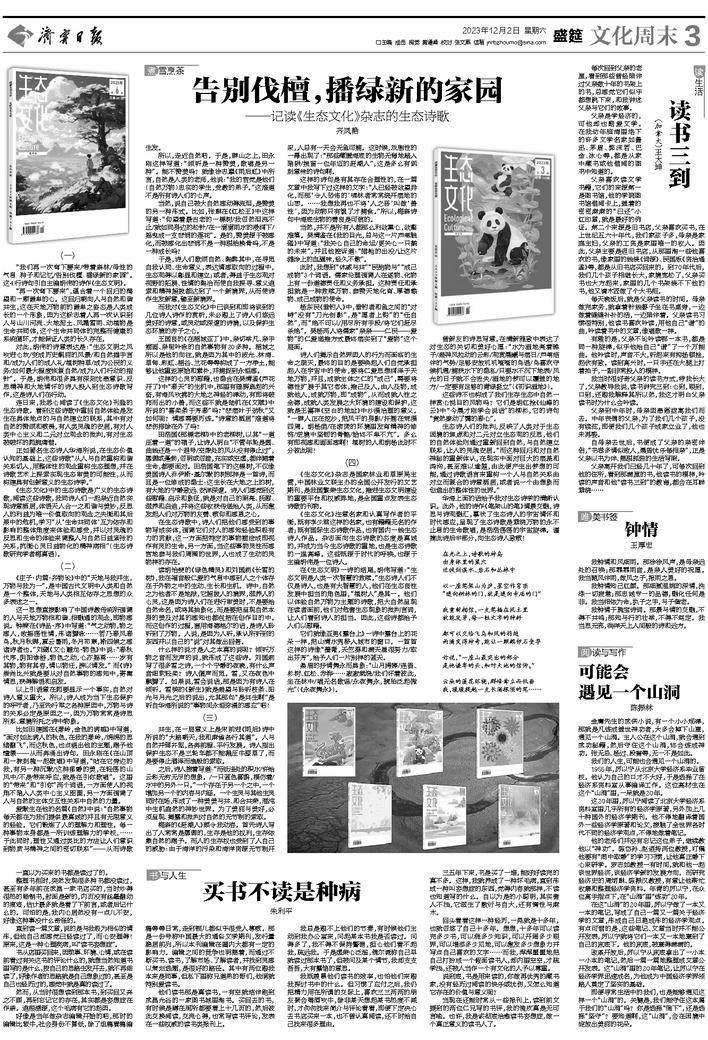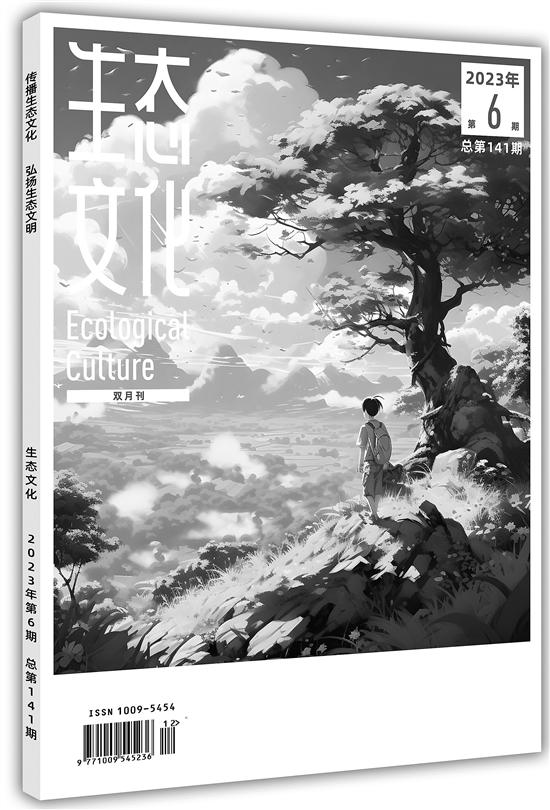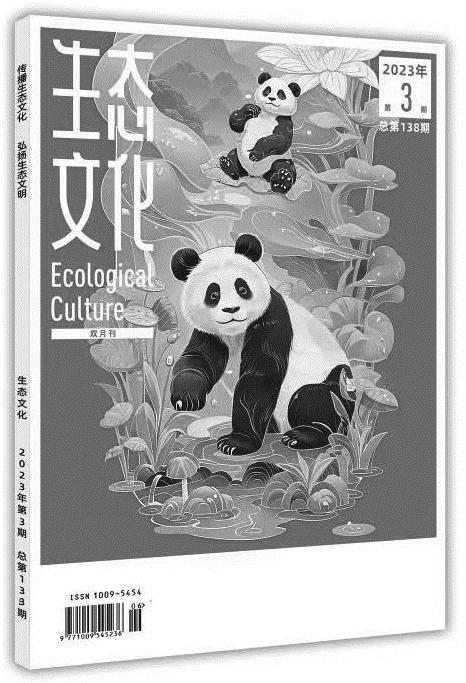齐凤艳
(一)
“我们再一次弯下腰来/带着森林/母性的气息 种子和记忆/告别伐檀 播绿新的家园”。这4行诗句引自主编胡伟的诗作《生态文明》。
“再一次弯下腰来”,蕴含着一个回归的渴望和一颗谦卑的心。这回归朝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在天地万物前的谦卑之姿态是人类成长的一个形象,因为这标志着人再一次认识到人与山川河流、大地泥土、风霜雪雨、动植物是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完整而健康的系统循环,才能保证人类的长久存在。
对此,胡伟的诗意表达是:“生态文明之风吹进心坎/变成历史靓丽的风景/和自然握手言和/成为人们的成人礼/植树种草/成为公民的义务/如何最大程度恢复自然/成为人们行动的指针”。于是,胡伟和很多具有深刻忧患意识、反思精神和大地情怀的诗人投入到生态诗歌写作,这是诗人们在行动。
连日来,我悉心阅读了《生态文化》刊登的生态诗歌。看到这些诗歌中重回自然体验是发生在具体地点的与自然建立的联系,其中有对自然的赞颂和敬畏,有人类灵魂的安居,有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观念的批判,有对生态被破坏的扼腕痛惜。
正如著名生态诗人华海所说,在生态价值认知的基础上,这些诗歌“从人与自然重构和谐关系切入,用整体性的观念重构生态理想,并在诗歌艺术上探索实现生态审美的可能性,从而构建具有创新意义的生态诗学。”
《生态文化》中的生态诗歌是广义的生态诗歌,阅读这些诗歌,我同诗人们一起亲近自然实现诗意栖居,体悟天人合一之和谐与美妙,反思人的利益为唯一价值取向的观念之失衡和其后果中的危机,学习“从‘生命共同体’互为依存和影响的整体角度来体验和感受,并以对灵魂的反思和生命的体验来调整人与自然日益紧张的关系,抗衡心灵日益物化的精神病相”(生态诗歌研究学者梅真语)。
(二)
《庄子·内篇·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中国古代文明中人类和自然是一个整体,天地与人类相互依存之思想的众多表述之一。
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诗教传统所强调的人与天地万物相和谐、相融通的观念,即物感说。钟嵘在《诗品·序》中写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而《诗》崇尚比兴就是要从对自然事物的感知中,寄寓情思,获得解悟和启发。
以上引语意在扼要显示一个事实,自然对诗人意义重大。所以,诗人成为当下生态保护的呼吁者,乃至先行军之各种原因中,万物与诗的关系必定是原因之一,因为万物常常是诗思所系、意境所托之诗中物象。
比如田建国在《秦岭,金色的诱惑》中写道,“面对如此诱人的秋色,在我的秦岭,/绵绵的思绪翻飞”,而这秋色,也点缀出他的主题,赐予他憧憬——从而奔涌出诗句。田永刚在《在山顶和一株刺槐一起歌唱》中写道,“站在它旁边的我,有另一种沉默/这种郁静的美,在轻荡的山风中/不是带来呼应,就是在引你歌唱”。这里的“带来”和“引你”两个词语,一方面使人的视角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囹圄,另一方面强调了人与自然的主体交互性关系中自然的力量。
爱默生在他的名篇《自然》中说:“自然事物每天都在为我们提供最真诚的并且有无限意义的经验。它们锻炼了人的理解力和理性。每一种事物本身都是一所训练理解力的学校,……于此同时,理性又通过类比的方法让人们意识到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诗歌生发。
所以,走近自然吧。于是,群山之上,田永刚这样写道:“倾听是一种赞美,歌唱是另一种”。能不赞美吗?就像徐志摩《雨后虹》中所言,自然是人类的老师,他说:“我的官觉是他们(自然万物)忠实的学生,受教的弟子。”这难道不是所有诗人们的心声。
当然,说自己被大自然感动得流泪,是赞美的另一种形式。比如,张琳在《红松王》中这样写道:“仰望着最古老的一棵树/我忽然泪流不止/就如同身边的松针/在一滴滴雨水的浸润下/摇曳成一支悲悯的莲花”。是的,赞美源于被感化,而被感化出悲悯不是一种脱胎换骨吗,不是一种成长吗?
于是,诗人们歌颂自然、陶醉其中,在寻觅自我认同、生命意义,表达情感取向的过程中,生态观得以彰显和建立;或者,得益于生态观对视野的拓展、性情的陶冶而使自我探寻、意义追索和精神超拔都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从而使诗作生发新意,臻至新境界。
而我对《生态文化》中已谈到和即将谈到的几位诗人诗作的赏析,未必跟上了诗人们悠远美好的诗意,或灵动或深邃的诗境,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赤子之心。
王国良的《在稻城亚丁》中,亲切举凡、亲手描画、亲昵吟咏的自然事物有20多种。稻城之所以是他的向往,就是因为其中的波光、林海、草甸、彩虹、稻谷、兰花等等构成了一方净土,能够让他重返原始和素朴,并捕捉到永恒感。
这样的心灵的慰藉,也隐含在吴清鉴《芦花开了》中“春天”的生机中,那里有翅膀扇起的兴奋,有海风吹拂的大地之神经的律动,有即将破卵而出的小兽,而这些不就是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喜柔条于芳春”吗?“悲落叶于劲秋”又如何呢?情感需要历练。“诗意的栖居”难道将悲伤排除在外了吗?
田浩国《那棵老柳》中的老柳树,以其“一道压着一道”的褶子,让诗人明白“不管年轮是圆、曲线还是一个逗号/空隙处的风从没有停止过”,孱弱或蓬勃,忽明或忽暗,充实或空虚,都伴随着生命,都要面对。田浩国笔下的这棵树,不仅像美国诗人乔伊斯·基尔默的树那样是一首诗,而且是一位修成的隐士:这生长在大地之上的树,有大地的宁静致远、安详深邃。诗人们感觉到这些慰藉、启示和象征,就是对自己的照亮、抚慰、滋养和启迪,并将这些收获传递给人类,从而激发起人们对万物的友善、敬仰和感恩之心。
在生态诗歌中,诗人们把他们感受到的事物写成实体,强调它们对人的感知经验积极有力的贡献,这一方面把特定的事物描绘成即视作有灵的生命,另一方面,当这些事物灵性而感官地参与我们周围的世界,人也成了生动的灵物样的存在。
读胡怡斐的《绿色精灵》和刘国莉《长雪的树》,我在福音般仁爱的气息中感到人之个体存在于外物之中的生动、生长和生机。诗中,自然之为他者不是地狱,它超拔人的境界,滋养人的心灵,这是因为诗人们在进行审美时,不是要给自然命名,或将其抽象化,而是要把呈现自然本身的美及对其的感知也都包括在创作目的中。而这创作的过程,套用海德格尔的话,是诗人聆听到了万物。人说,是因为人听,承认所听到的东西并以自己的“说”对其做出回答。
什么样的说才是人之本真的说呢?倾听万物之音而发声的说,就形成了这些诗。刘国莉写了很多雪之诗,一个个宁静的夜晚,有什么声音细软轻柔?诗人循声而觅。雪,又在夜色中飘舞了。如果说,雪会说话,那是因为有诗人在倾听。雪鸮的《新生》就是凝望与聆听枝条、阳光与月光之后的说出,尤其那句“是共生啊”是听自华海所说的“事物间永恒弥漫的感应”吧!
(三)
共生,在一层意义上是宋前进《雨后》诗中所说的“大路朝天,我和麻雀各行其道”。人与自然并驾齐驱,各奔前程、平行发展。诗人指出保护生态不是三轮车都不能碾压牛膝草了,而是要停止涸泽而渔般的索取。
之后,诗人接着写道:“而低洼处的积水/许给云彩无穷无尽的想象。/一只蓝色喜鹊,模仿着/水中的另外一只。”一个存在于另一个之中,一个增加另一个的内容与内涵。一个生灵与其他生灵同时在场,形成了一种美美与共、和合共荣,混沌中生机盎然的神妙世界。为了美丽与美好,必须呈现、揭露和批判对自然的无节制的索取。
梅森的《赶潮人》颇令我动容。首先诗人写出了人常常是孱弱的,生存是他的权利,生存依赖自然的赐予。而人的生存权也受到了人自己的威胁:由于海洋的污染和海洋资源无节制开采,人总有一天会无鱼可捕。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那些藏匿海底的生物无悔地踏入陷阱/挽留一位年迈的赶潮人”,这是多么有讽刺意味的诗句啊。
这样的诗句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在一篇文章中我写下过这样的文字:“人已经被欲望异化,而那‘令人恐怖的’啸林者常常绕开落地的山枣。……我想我再也不将‘人之恶’叫做‘兽性’,因为动物只有饿了才捕食。”所以,梅森诗句中海底生物的善良是可信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利欲熏心,欲壑难填。吴清鉴在《我的目光,总与这一片芦苇触碰》中写道:“我关心自己的命运/更关心一只鹤的未来”,并且他控诉道:“猎枪的出没/让这片滩涂上的血腥味,经久不散”。
此时,我想到“休戚与共”“民胞物与”“成己成物”3个词语。儒家伦理强调人在遂物、化物上有一份道德责任和义务承担。这种责任和承担就是一种救赎万物、参赞天地化育、厚德载物、成己成物的使命。
杨东民《垂钓人》中,垂钓者和鱼之间的“对峙”没有“刀光剑影”,是“愿者上钩”的“任自然”,而“绝不可以/用尽所有手段/将它们赶尽杀绝”。吴杨两人将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仁爱递推方式最终落实到了“爱物”这个层面。
诗人们揭示自然界因人的行为而面临的生命之陨灭,最终的目的是要唤起人们自觉承担起人在宇宙中的使命,要将仁爱思想润泽于天地万物,并且,成就主体之仁的“成己”,需要将德性扩展于其它客体,推己及人,由人及物,成就他人,成就万物,即“成物”,从而成就人性之全德,成就人类发展之大环境的建设和保护,这就是王富祥《空白的地址》中沙漠治理的意义。“一群人正在挖沙,把风干的身影/扦插在荒漠四周。胡杨苗/在滚烫的环境里发育精神的修饰/逆境中坚韧的骨骼/始终不卑不亢”。多么有即视感和画面感啊!植树的人和胡杨此时不分彼此呢!
(四)
《生态文化》杂志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管,中国林业文联主办的全国公开发行的文艺期刊,是我国繁荣生态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和权威阵地,是全国重点发表生态诗歌的刊物。
《生态文化》注意名家和认真写作者的平衡,既有李少君这样的名家,也有籍籍无名的作者;既有国际生态诗歌作品,也有国内一线生态诗人作品。杂志面向生态诗歌的态度是真诚的,并成为当今生态诗歌的重地,也是生态诗歌的一座高峰。这些既源于时代的呼唤,也源于主编胡伟是一位诗人。
在《生态文明》一诗的结尾,胡伟写道:“生态文明是人类一次智慧的救赎。”生态诗人们不仅是诗人,也是有大智慧的人,他们在生态良性发展中担当的角色里,“植树人”是其一。他们以体验自然万物为主题的诗歌,把大自然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们对危害生态现象的批判言词,让人们看到诗人的担当。因此,这些诗都给予人们以慰藉。
它们就像亚男《露台上》一诗中露台上的花朵一样,把山清水秀移入城市的窗口。一首首这样的诗像“蔷薇,天竺葵和满天星很努力/取出芬芳”,给予人们一片别样的蓝天。
桑眉的抒情隽永而具象:“山月娉婷/连香、杉树、红松、赤桦……寂寂燃烧/我们怀着彼此,坐在林中/唱无名歌谣/永夜隽永,琥珀泛起微光”(《永夜隽永》)。
曾新友的诗思写意,在清新雅致中表达了对生态的关切和美好心愿:“水为湿地亮着眸子/凝神风拉动的云彩/观赏晨曦与落日/芦苇结伴的气势/足够安放叽叽喳喳的鸟语/鸟喜欢守候机遇/捕获水下的隐私/只要水不沉下地表/风光的日子就不会丢失/湿地的梦可以覆盖的地方/一定要有足够的青绿挺立”(《初识湿地》)。
这些诗不也构成了我们生存生态中自然一样赏心悦目的风物吗?它们是胡红拴《仙峰的云》中“今晨才刚学会说话”的柳杉,它的诗句“竟然撩动了霭的春心”。
生态诗人们的批判,反映了人类对于生态困境的焦虑和对二元对立生态观的反思,他们的自然体验则通过重新回到自然,与自然建立联系,让人的灵魂安居。“而这种回归和对自然神秘的重新体认,在现实中面对巨大的落差和鸿沟,甚至难以逾越,由此便产生出梦想的可能,通过诗歌语言来重构一个人与自然关系由对立而复合的诗意栖居,或者说一个由想象而创造出的整体性的世界。”
华海上面的话给予我对生态诗学的清晰认识。此外,他的诗作《笔架山的笔》情景交融,诗思与诗观融汇,摹状了生态诗人的宇宙情怀和时代感应,呈现了生态诗歌是萦绕万物的永不止息的生命歌唱,是浩浩荡荡的宇宙旋律。谨摘此诗后半部分,向生态诗人致敬!
在光之上,诗歌的神鸟
由身体里的巢穴
迁徙到溪水、岩石和丛林中
以一座笔架山为庐,星空作穹顶
“通向树林的门,就是通向寺庙的门”
我重新相信,一支笔插在泥土里
就能发芽,每一粒文字的种籽
都可以交给飞鸟和风的羽翅
雨滴变得神奇,能让一颗鹅卵石受孕
你说,“一座山最突出的部分
是他谦卑的头,和对大地的信仰。”
云朵的莲花环绕,群峰耸立而低垂
我,缓缓提起一支长满根须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