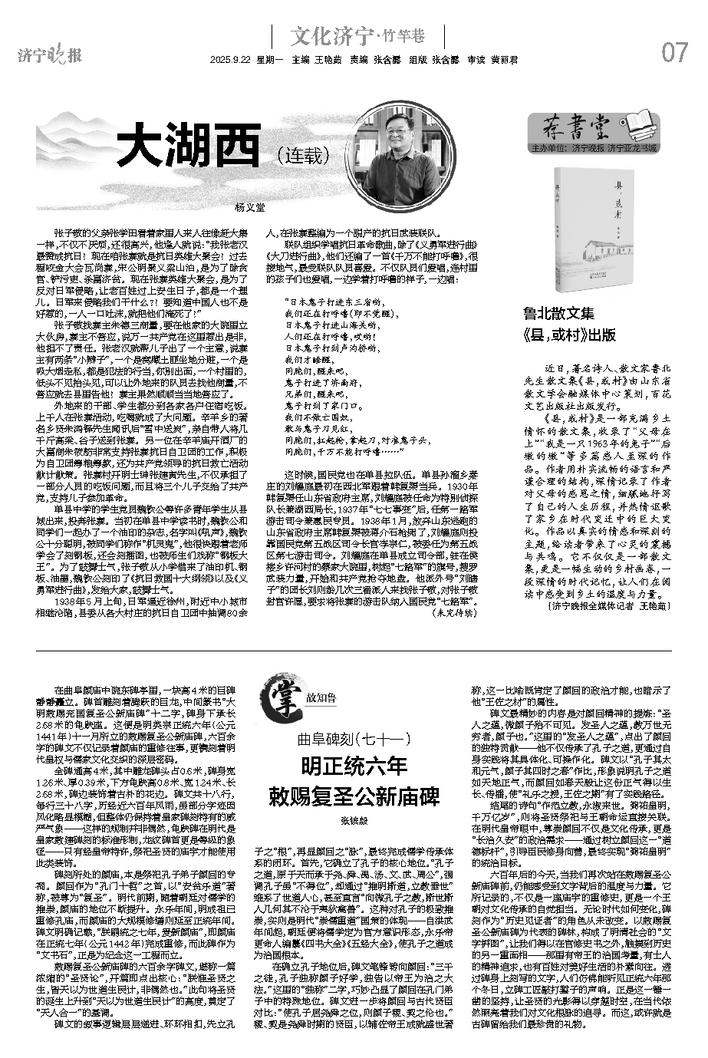张镔毅
在曲阜颜庙中院东碑亭里,一块高4米的巨碑静静矗立。碑首雕刻着腾跃的巨龙,中间篆书“大明敕赐兖国复圣公新庙碑”十二字,碑身下承长2.68米的龟趺座。这便是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十一月所立的敕赐复圣公新庙碑,六百余字的碑文不仅记录着颜庙的重修往事,更镌刻着明代皇权与儒家文化交织的深层密码。
全碑通高4米,其中雕龙碑头占0.6米,碑身宽1.26米、厚0.39米,下方龟趺高0.8米、宽1.24米、长2.68米,碑边装饰着古朴的花边。碑文共十八行,每行三十八字,历经近六百年风雨,虽部分字迹因风化略显模糊,但整体仍保持着皇家碑刻特有的威严气象——这样的规制并非偶然,龟趺碑在明代是皇家敕建碑刻的标准形制,龙纹碑首更是等级的象征——只有经皇帝特许,祭祀圣贤的庙宇才能使用此类装饰。
碑刻所处的颜庙,本是祭祀孔子弟子颜回的专祠。颜回作为“孔门十哲”之首,以“安贫乐道”著称,被尊为“复圣”。明代前期,随着朝廷对儒学的推崇,颜庙的地位不断提升。永乐年间,明成祖已重修孔庙,而颜庙的大规模修缮则延至正统年间。碑文明确记载,“朕嗣统之七年,爰新颜庙”,即颜庙在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完成重修,而此碑作为“文书石”,正是为纪念这一工程而立。
敕赐复圣公新庙碑的六百余字碑文,堪称一篇浓缩的“圣贤论”,开篇即点出核心:“朕惟圣贤之生,皆天以为世道生民计,非偶然也。”此句将圣贤的诞生上升到“天以为世道生民计”的高度,奠定了“天人合一”的基调。
碑文的叙事逻辑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先立孔子之“根”,再显颜回之“脉”,最终完成儒学传承体系的闭环。首先,它确立了孔子的核心地位。“孔子之道,原于天而承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强调孔子虽“不得位”,却通过“推明斯道,立教垂世”维系了世道人心,甚至直言“向微孔子之教,斯世斯人几何其不沦于夷狄禽兽”。这种对孔子的极致推崇,实则是明代“崇儒重道”国策的体现——自洪武年间起,朝廷便将儒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永乐帝更命人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使孔子之道成为治国根本。
在确立孔子地位后,碑文笔锋转向颜回:“三千之徒,孔子独称颜子好学,独告以帝王为治之大法。”这里的“独称”二字,巧妙凸显了颜回在孔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碑文进一步将颜回与古代贤臣对比:“使孔子居尧舜之位,则颜子稷、契之伦也。”稷、契是尧舜时期的贤臣,以辅佐帝王成就盛世著称,这一比喻既肯定了颜回的政治才能,也暗示了他“王佐之材”的属性。
碑文最精妙的内容是对颜回精神的提炼:“圣人之蕴,微颜子殆不可见。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子也。”这里的“发圣人之蕴”,点出了颜回的独特贡献——他不仅传承了孔子之道,更通过自身实践将其具体化、可操作化。碑文以“孔子其太和元气,颜子其四时之春”作比,形象说明孔子之道如天地正气,而颜回如春天般让这份正气得以生长、传播,使“礼乐之授,王佐之期”有了实践路径。
结尾的诗句“作范立教,永淑来世。弼祐皇明,千万亿岁”,则将圣贤祭祀与王朝命运直接关联。在明代皇帝眼中,尊崇颜回不仅是文化传承,更是“长治久安”的政治需求——通过树立颜回这一“道德标杆”,引导臣民修身向善,最终实现“弼祐皇明”的统治目标。
六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站在敕赐复圣公新庙碑前,仍能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温度与力量。它所记录的,不仅是一座庙宇的重修史,更是一个王朝对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碑刻作为“历史见证者”的角色从未改变。以敕赐复圣公新庙碑为代表的碑林,构成了明清社会的“文字拼图”,让我们得以在官修史书之外,触摸到历史的另一重面相——那里有帝王的治国考量,有士人的精神追求,也有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透过碑身上刻写的文字,人们仿佛能听见正统六年那个冬日,立碑工匠敲打錾子的声响。正是这一锤一凿的坚持,让圣贤的光影得以穿越时空,在当代依然照亮着我们对文化根脉的追寻。而这,或许就是古碑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