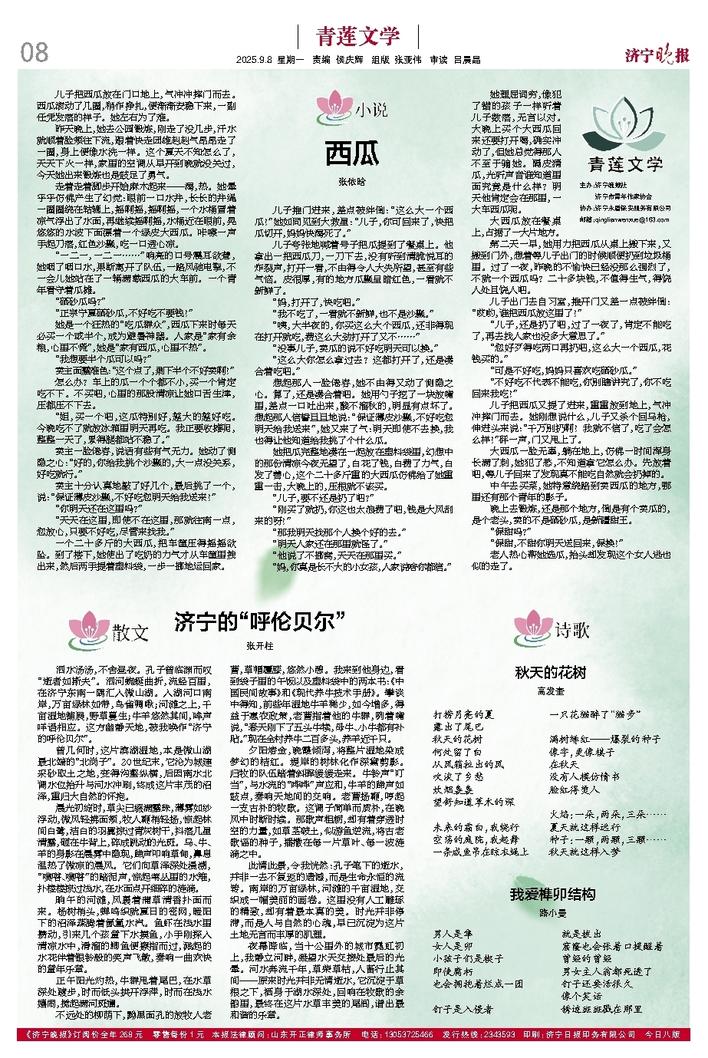张开柱
泗水汤汤,不舍昼夜。孔子曾临渊而叹“逝者如斯夫”。泗河蜿蜒曲折,流经百里,在济宁东南一隅汇入微山湖。入湖河口南岸,万亩绿林如带,鸟雀啁啾;河滩之上,千亩湿地铺展,野草蔓生;牛羊悠然其间,哞声咩语相应。这方幽静天地,被我唤作“济宁的呼伦贝尔”。
曾几何时,这片滨湖湿地,本是微山湖最北端的“北岗子”。20世纪末,它沦为城建采砂取土之地,变得沟壑纵横,后因南水北调水位抬升与河水冲刷,终成这片丰茂的沼泽,重归大自然的怀抱。
晨光初绽时,草尖已缀满露珠,薄雾如纱浮动,微风轻拂面颊,牧人鞭梢轻扬,惊起林间白鹭,洁白的羽翼掠过青灰树干,抖落几星清露,砸在牛背上,碎成跳动的光斑。马、牛、羊的身影在晨雾中隐现,蹄声叩响草甸,鼻息温热了微凉的晨风。它们向草泽深处漫溯,“噗嗒、噗嗒”的踏泥声,惊起苇丛里的水雉,扑棱棱掠过浅水,在水面点开细碎的涟漪。
晌午的河滩,风裹着蒲草清香扑面而来。杨树梢头,蝉鸣织就夏日的密网,暖阳下的沼泽蒸腾着氤氲水汽。鱼虾在浅水里攒动,引来几个孩童下水摸鱼,小手刚探入清凉水中,滑溜的鲫鱼便擦指而过,溅起的水花伴着银铃般的笑声飞散,奏响一曲欢快的童年乐章。
正午阳光灼热,牛群甩着尾巴,在水草深处踱步,时而低头拱开浮萍,时而在浅水嬉闹,搅起满河斑斓。
不远处的柳荫下,黝黑面孔的放牧人老曹,草帽覆膝,悠然小憩。我来到他身边,看到袋子里的午饭以及塑料袋中的两本书:《中国民间故事》和《现代养牛技术手册》。攀谈中得知,前些年湿地牛羊稀少,如今增多,得益于惠农政策,老曹指着他的牛群,咧着嘴说,“春天刚下了五头牛犊,母牛、小牛都有补贴。”现在全村养牛二百多头,养羊近千只。
夕阳熔金,晚霞倾泻,将整片湿地染成梦幻的桔红。堤岸的树林化作深黛剪影。归牧的队伍踏着斜晖缓缓走来。牛铃声“叮当”,与水流的“哗哗”声应和,牛羊的蹄声如鼓点,奏响天地间的交响。老曹扬鞭,哼起一支古朴的牧歌。这调子简单而质朴,在晚风中时断时续。那歌声粗粝,却有着穿透时空的力量,如草茎破土,似游鱼逆流,将古老歌谣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草叶、每一波涟漪之中。
此情此景,令我恍然:孔子笔下的逝水,并非一去不复返的遗憾,而是生命永恒的流转。南岸的万亩绿林,河滩的千亩湿地,交织成一幅美丽的画卷。这里没有人工雕琢的精致,却有着最本真的美。时光并非停滞,而是人与自然的心魂,早已沉淀为这片土地无言而丰厚的肌理。
夜幕降临,当十公里外的城市霓虹初上,我静立河畔,凝望水天交接处最后的光晕。河水奔流千年,草荣草枯,人畜行止其间——原来时光并非无情逝水,它沉淀于草根之下,栖身于湖水深处,回响在牧歌的余韵里,最终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尾闾,谱出最和谐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