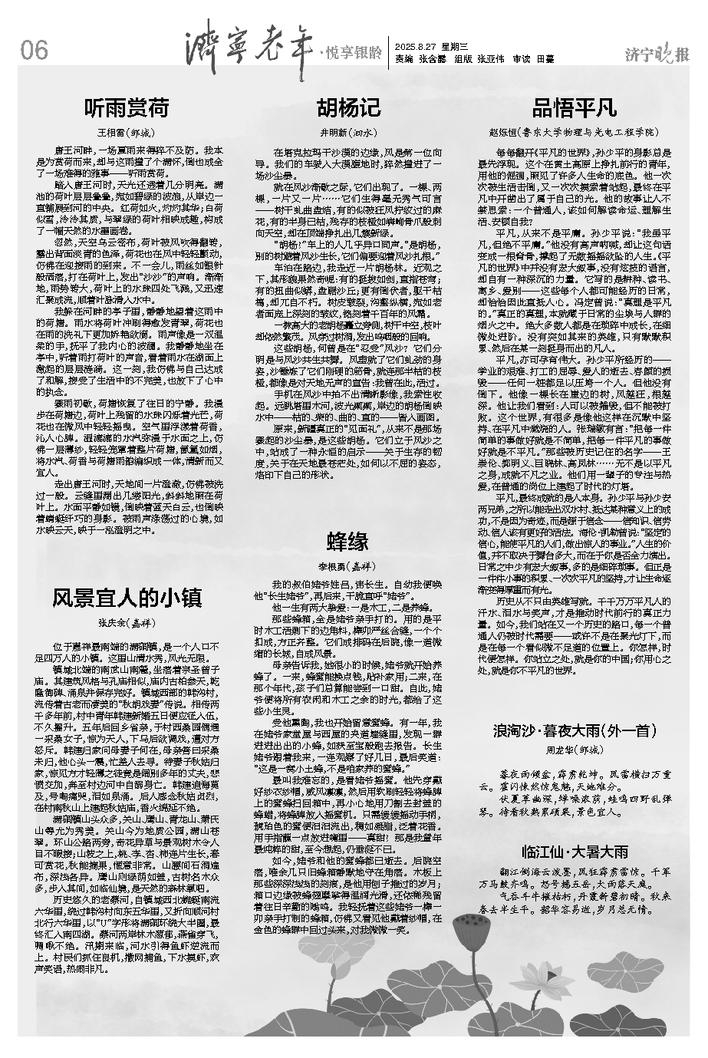井明新(泗水)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风是第一位向导。我们的车驶入大漠腹地时,猝然撞进了一场沙尘暴。
就在风沙渐歇之际,它们出现了。一棵、两棵,一片又一片……它们生得毫无秀气可言——树干虬曲盘结,有的似被狂风拧绞过的麻花,有的半身已枯,残存的枝桠如嶙峋骨爪般刺向天空,却在顶端挣扎出几簇新绿。
“胡杨!”车上的人几乎异口同声。“是胡杨,别的树避着风沙生长,它们偏要迎着风沙扎根。”
车泊在路边,我走近一片胡杨林。近观之下,其形貌果然奇崛:有的挺拔如剑,直指苍穹;有的扭曲似蟒,盘踞沙丘;更有倒伏者,躯干枯槁,却兀自不朽。树皮皲裂,沟壑纵横,宛如老者面庞上深刻的皱纹,铭刻着千百年的风霜。
一株高大的老胡杨矗立旁侧,树干中空,枝叶却依然繁茂。风穿过树洞,发出呜咽般的回响。
这些胡杨,何曾是在“忍受”风沙?它们分明是与风沙共生共舞。风塑就了它们虬劲的身姿,沙锤炼了它们刚硬的筋骨,就连那半枯的枝桠,都像是对天地无声的宣告:我曾在此,活过。
手机在风沙中拍不出清晰影像,我索性收起。远眺塔里木河,波光粼粼,岸边的胡杨倒映水中——枯的、荣的、曲的、直的——皆入画图。
原来,新疆真正的“见面礼”,从来不是那场骤起的沙尘暴,是这些胡杨。它们立于风沙之中,站成了一种永恒的启示——关于生存的韧度,关于在天地最苍茫处,如何以不屈的姿态,烙印下自己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