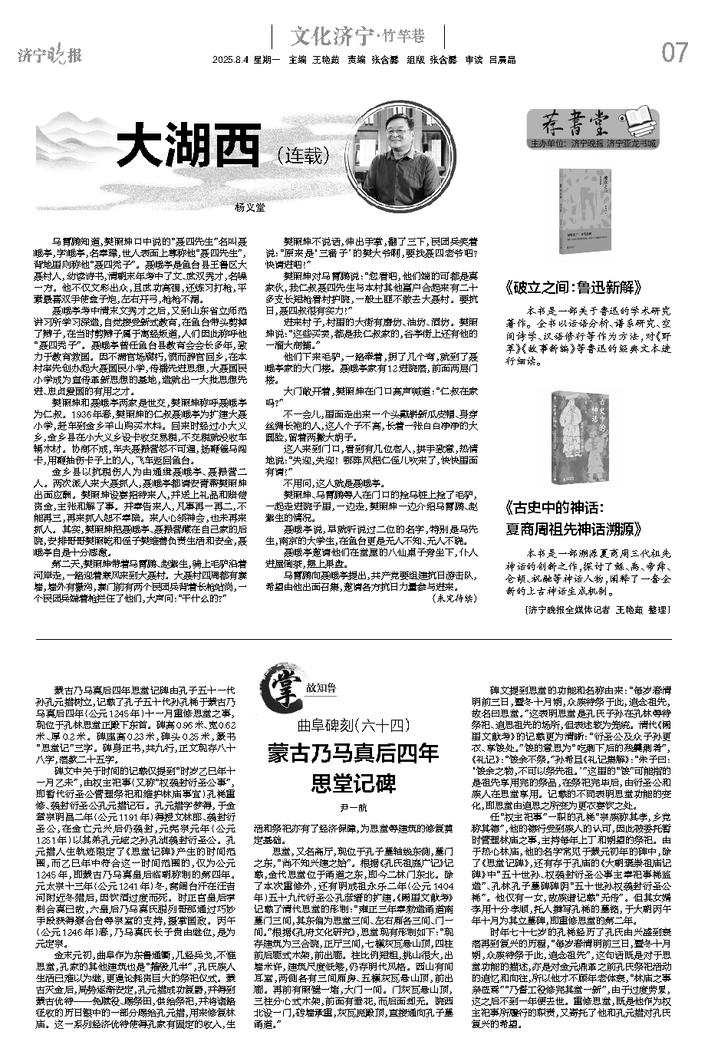尹一航
蒙古乃马真后四年思堂记碑由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树立,记载了孔子五十代孙孔桸于蒙古乃马真后四年(公元1245年)十一月重修思堂之事,现位于孔林思堂正殿下东首。碑高0.96米、宽0.62米、厚0.2米。碑座高0.23米,碑头0.25米,篆书“思堂记”三字。碑身正书,共九行,正文现存八十八字,落款二十五字。
碑文中关于时间的记载仅提到“时岁乙巳年十一月乙未”,由权主祀事(又称“权袭封衍圣公事”,即暂代衍圣公管理祭祀和维护林庙事宜)孔桸重修、袭封衍圣公孔元措记石。孔元措字梦得,于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得授文林郎、袭封衍圣公,在金亡元兴后仍袭封,元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以其弟孔元綋之孙孔浈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人生轨迹限定了《思堂记碑》产生的时间范围,而乙巳年中符合这一时间范围的,仅为公元1245年,即蒙古乃马真皇后临朝称制的第四年。元太宗十三年(公元1241年)冬,窝阔台汗在汪吉河附近冬猎后,因饮酒过度而死。时正宫皇后孛剌合真已故,六皇后乃马真氏脱列哥那通过巧妙手段获得察合台等宗室的支持,摄掌国政。丙午(公元1246年)春,乃马真氏长子贵由继位,是为元定宗。
金末元初,曲阜作为东鲁通衢,几经兵戈,不惟思堂,孔家的其他建筑也是“摧毁几半”,孔氏族人生活已难以为继,更遑论耗资巨大的祭祀仪式。蒙古灭金后,局势逐渐安定,孔元措成功复爵,并得到蒙古优待——免赋役、赐祭田,供给祭祀,并将诸路征收的历日银中的一部分赐给孔元措,用来修复林庙。这一系列经济优待使得孔家有固定的收入,生活和祭祀亦有了经济保障,为思堂等建筑的修复奠定基础。
思堂,又名斋厅,现位于孔子墓轴线东侧,墓门之东,“尚不知兴建之始”。根据《孔氏祖庭广记》记载,金代思堂位于甬道之东,即今二林门东北。除了本次重修外,还有明成祖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五十九代衍圣公孔彦缙的扩建。《阙里文献考》记载了清代思堂的形制:“雍正三年奉勑造甬道南墓门三间,其东偏为思堂三间、左右厢各三间、门一间。”根据《孔府文化研究》,思堂现有形制如下:“现存建筑为三合院,正厅三间,七檩灰瓦悬山顶,四柱前后廊式木架,前出廊。柱比例短粗,挑山很大,出墙米许,建筑尺度低矮,仍存明代风格。西山有间耳室,两侧各有三间厢房、五檩灰瓦悬山顶,前出廊。再前有照壁一堵,大门一间。门灰瓦悬山顶,三柱分心式木架,前面有垂花,而后面却无。院西北设一门,砖墙承重,灰瓦庑殿顶,直接通向孔子墓甬道。”
碑文提到思堂的功能和名称由来:“每岁春清明前三日,暨冬十月朔,众族待祭于此,追念祖先,故名曰思堂。”这表明思堂是孔氏子孙在孔林等待祭祀、追思祖先的场所,但表述较为笼统。清代《阙里文献考》的记载更为清晰:“衍圣公及众子孙更衣、享馂处。”馂的意思为“吃剩下后的残羹剩肴”,《礼记》:“馂余不祭。”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子曰:‘馂余之物,不可以祭先祖。’”这里的“馂”可能指的是祖先享用完的祭品,在祭祀完毕后,由衍圣公和族人在思堂享用。记载的不同表明思堂功能的变化,即思堂由追思之所变为更衣宴饮之处。
任“权主祀事”一职的孔桸“宗族称其孝,乡党称其德”,他的德行受到族人的认可,因此被委托暂时管理林庙之事,主持每年上丁和朔望的祭祀。由于热心林庙,他的名字常见于蒙元初年的碑中,除了《思堂记碑》,还有存于孔庙的《大朝褒崇祖庙记碑》中“五十世孙、权袭封衍圣公事主奉祀事桸监造”、孔林孔子墓碑碑阴“五十世孙权袭封衍圣公桸”。他仅有一女,故族谱记载“无传”。但其女婿李用十分孝顺,托人撰写孔桸的墓铭,于大朝丙午年十月为其立墓碑,即重修思堂的第二年。
时年七十七岁的孔桸经历了孔氏由兴盛到衰落再到复兴的历程,“每岁春清明前三日,暨冬十月朔,众族待祭于此,追念祖先”,这句话既是对于思堂功能的描述,亦是对金元鼎革之前孔氏祭祀活动的追忆和向往,所以他才不顾年老体衰,“林庙之事亲莅焉”“乃督工役修完其堂一新”,由于过度劳累,这之后不到一年便去世。重修思堂,既是他作为权主祀事所履行的职责,又寄托了他和孔元措对孔氏复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