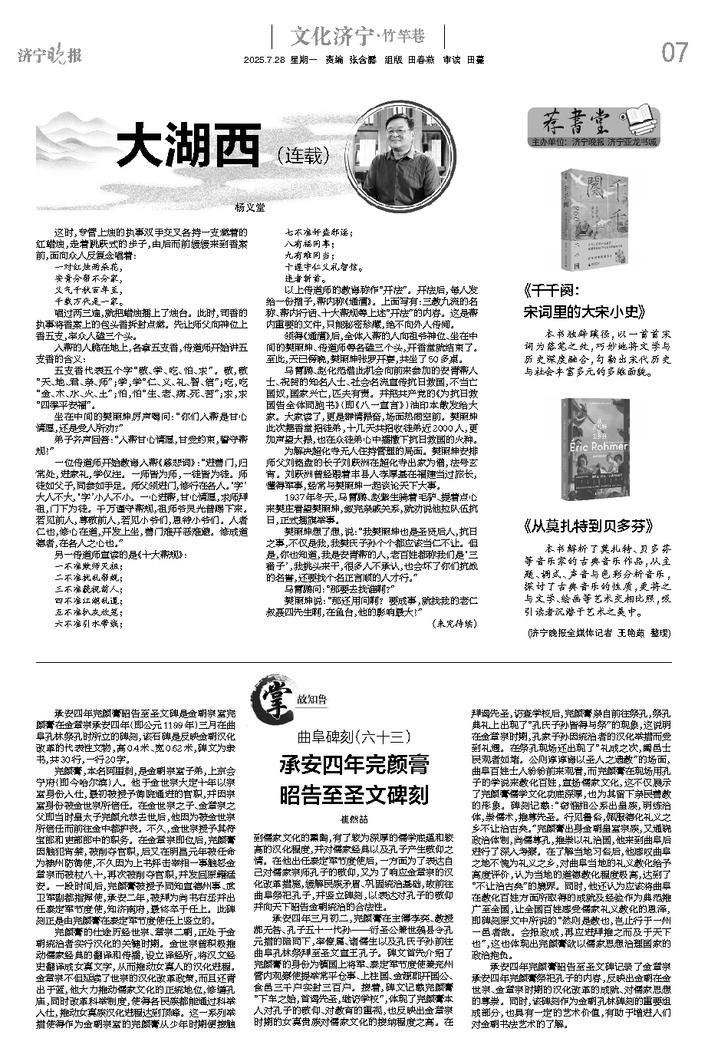崔然喆
承安四年完颜膏昭告至圣文碑是金朝宗室完颜膏在金章宗承安四年(即公元1199年)三月在曲阜孔林祭孔时所立的碑刻,该石碑是反映金朝汉化改革的代表性文物,高0.4米、宽0.62米,碑文为隶书,共30行,一行20字。
完颜膏,本名阿里刺,是金朝宗室子弟,上京会宁府(即今哈尔滨)人。他于金世宗大定十年以宗室身份入仕,最初被授予御院通进的官职,并因宗室身份被金世宗所信任。在金世宗之子、金章宗之父即当时皇太子完颜允恭去世后,他因为被金世宗所信任而前往金中都护丧。不久,金世宗授予其符宝郎和吏部郎中的职务。在金章宗即位后,完颜膏因触犯宵禁,被削夺官职,后又在明昌元年被任命为棣州防御使,不久因为上书抨击宰相一事触怒金章宗而被杖八十,再次被削夺官职,并发回原籍猛安。一段时间后,完颜膏被授予同知宣德州事、武卫军副都指挥使,承安二年,被拜为尚书右丞并出任泰定军节度使,知济南府,最终卒于任上。此碑刻正是由完颜膏在泰定军节度使任上竖立的。
完颜膏的仕途历经世宗、章宗二朝,正处于金朝统治者实行汉化的关键时期。金世宗曾积极推动儒家经典的翻译和传播,设立译经所,将汉文经史翻译成女真文字,从而推动女真人的汉化进程。金章宗不但延续了世宗的汉化改革政策,而且还青出于蓝,他大力推动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修缮孔庙,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使得各民族都能通过科举入仕,推动女真族汉化进程达到顶峰。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作为金朝宗室的完颜膏从少年时期便接触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有了较为深厚的儒学底蕴和较高的汉化程度,并对儒家经典以及孔子产生敬仰之情。在他出任泰定军节度使后,一方面为了表达自己对儒家宗师孔子的敬仰,又为了响应金章宗的汉化改革措施,缓解民族矛盾、巩固统治基础,故前往曲阜祭祀孔子,并竖立碑刻,以表达对孔子的敬仰并向天下昭告金朝统治的合法性。
承安四年三月初二,完颜膏在主簿李奕、教授郝无咎、孔子五十一代孙——衍圣公兼世袭县令孔元措的陪同下,率僚属、诸儒生以及孔氏子孙前往曲阜孔林祭拜至圣文宣王孔子。碑文首先介绍了完颜膏的身份为镇国上将军、泰定军节度使兼兖州管内观察使提举常平仓事、上柱国、金源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实封三百户。接着,碑文记载完颜膏“下车之始,首谒先圣,继访学校”,体现了完颜膏本人对孔子的敬仰、对教育的重视,也反映出金章宗时期的女真贵族对儒家文化的接纳程度之高。在拜谒先圣,访查学校后,完颜膏亲自前往祭孔,祭孔典礼上出现了“孔氏子孙皆得与祭”的现象,这说明在金章宗时期,孔家子孙因统治者的汉化举措而受到礼遇。在祭孔现场还出现了“礼成之次,阖邑士民观者如堵。公则谆谆诲以圣人之遗教”的场面,曲阜百姓士人纷纷前来观看,而完颜膏在现场用孔子的学说来教化百姓,宣扬儒家文化,这不仅展示了完颜膏儒学文化功底深厚,也为其留下亲民善教的形象。碑刻记载:“窃惟相公系出皇族,明练治体,崇儒术,推尊先圣。行见鲁俗,佩服德化礼义之乡不让治古矣。”完颜膏出身金朝皇室宗族,又通晓政治体制,尚儒尊孔,推崇以礼治国,他来到曲阜后进行了深入考察。在了解当地习俗后,他感叹曲阜之地不愧为礼义之乡,对曲阜当地的礼义教化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当地的道德教化程度极高,达到了“不让治古矣”的境界。同时,他还认为应该将曲阜在教化百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作为典范推广至全国,让全国百姓感受儒家礼义教化的恩泽,即碑刻原文中所说的“然则是教也,岂止行于一州一邑者哉。会报政成,再应进拜推之而及于天下也”,这也体现出完颜膏欲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的政治抱负。
承安四年完颜膏昭告至圣文碑记录了金章宗承安四年完颜膏祭祀孔子的内容,反映出金朝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的汉化改革的成就、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同时,该碑刻作为金朝孔林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有助于增进人们对金朝书法艺术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