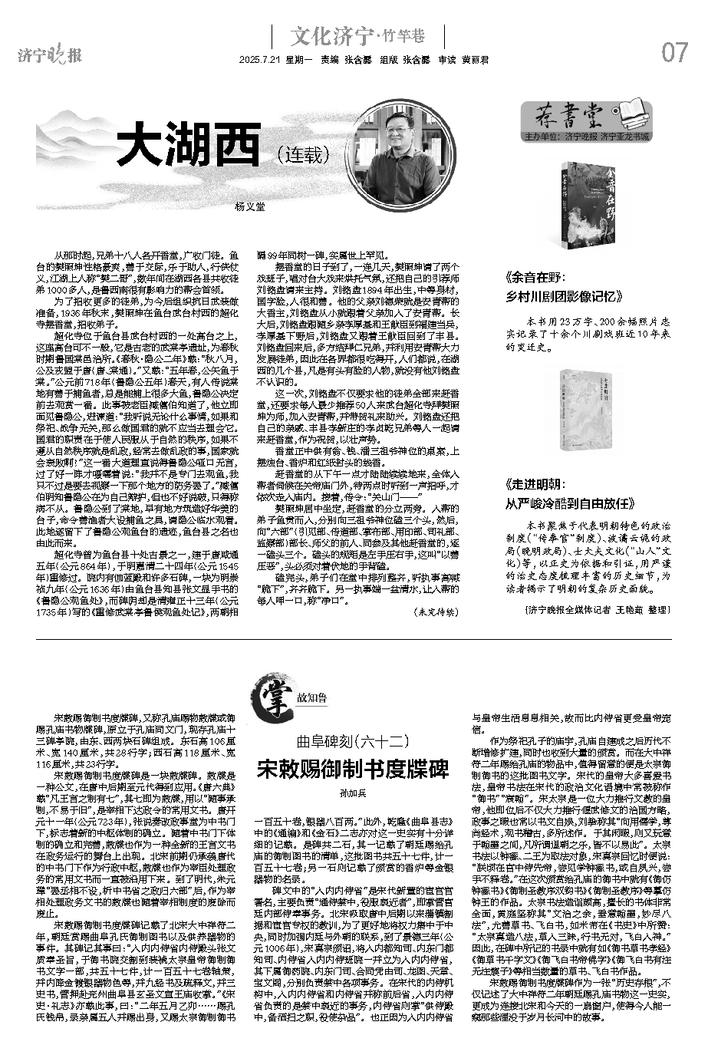孙加兵
宋敕赐御制书度牒碑,又称孔庙赐物敕牒或御赐孔庙书物牒碑,原立于孔庙同文门,现存孔庙十三碑亭院,由东、西两块石碑组成。东石高106厘米、宽140厘米,共28行字;西石高118厘米、宽116厘米,共23行字。
宋敕赐御制书度牒碑是一块敕牒碑。敕牒是一种公文,在唐中后期至元代得到应用。《唐六典》载“凡王言之制有七”,其七即为敕牒,用以“随事承制,不易于旧”,是宰相下达政令的常用文书。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标志着新的中枢体制的确立。随着中书门下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敕牒也作为一种全新的王言文书在政务运行的舞台上出现。北宋前期仍承袭唐代的中书门下作为行政中枢,敕牒也作为宰臣处理政务的常用文书而一直被沿用下来。到了明代,朱元璋“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后,作为宰相处理政务文书的敕牒也随着宰相制度的废除而废止。
宋敕赐御制书度牒碑记载了北宋大中祥符二年,朝廷赏赐曲阜孔氏御制图书以及供养器物的事件。其碑记其事曰:“入内内侍省内侍殿头张文质奉圣旨,于御书院交割到装裭太宗皇帝御制御书文字一部,共五十七件,计一百五十七卷轴策,并内降金镀银器物色等,并九经书及疏释文,并三史书,管押赴兖州曲阜县玄圣文宣王庙收掌。”《宋史·礼志》亦载此事,曰:“二年五月乙卯……赐孔氏钱帛,录亲属五人并赐出身,又赐太宗御制御书一百五十卷,银器八百两。”此外,乾隆《曲阜县志》中的《通编》和《金石》二志亦对这一史实有十分详细的记载。是碑共二石,其一记载了朝廷赐给孔庙的御制图书的清单,这批图书共五十七件,计一百五十七卷;另一石则记载了颁赏的香炉等金银器物的名录。
碑文中的“入内内侍省”是宋代新置的宦官官署名,主要负责“通侍禁中,役服亵近者”,即掌管宫廷内部侍奉事务。北宋吸取唐中后期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教训,为了更好地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同时加强内廷与外朝的联系,到了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宋真宗颁诏,将入内都知司、内东门都知司、内侍省入内内侍班院一并立为入内内侍省,其下属御药院、内东门司、合同凭由司、龙图、天章、宝文阁,分别负责禁中各项事务。在宋代的内侍机构中,入内内侍省和内侍省并称前后省,入内内侍省负责的是禁中亵近的事务,内侍省则掌“供侍殿中,备洒扫之职,役使杂品”。也正因为入内内侍省与皇帝生活息息相关,故而比内侍省更受皇帝宠信。
作为祭祀孔子的庙宇,孔庙自建成之后历代不断增修扩建,同时也收到大量的颁赏。而在大中祥符二年赐给孔庙的物品中,值得留意的便是太宗御制御书的这批图书文字。宋代的皇帝大多喜爱书法,皇帝书法在宋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常被称作“御书”“宸翰”。宋太宗是一位大力推行文教的皇帝,他即位后不仅大力推行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政事之暇也常以书文自娱,刘挚称其“向用儒学,尊尚经术,观书稽古,多所述作。于其闲暇,则又玩意于翰墨之间,凡所谓退朝之乐,皆不以易此”。太宗书法以钟繇、二王为取法对象,宋真宗回忆时便说:“朕顷在宫中侍先帝,尝见学钟繇书,或自夙兴,尝手不释卷。”在这次颁赏给孔庙的御书中就有《御仿钟繇书》《御制圣教序双钩书》《御制圣教序》等摹仿钟王的作品。太宗书法造诣颇高,擅长的书体非常全面,黄庭坚称其“文治之余,垂意翰墨,妙尽八法”,尤善草书、飞白书,如米芾在《书史》中所赞:“太宗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书无对,飞白入神。”因此,在碑中所记的书录中就有如《御书草书孝经》《御草书千字文》《御飞白书帝佛字》《御飞白书有注无注簇子》等相当数量的草书、飞白书作品。
宋敕赐御制书度牒碑作为一张“历史存根”,不仅记述了大中祥符二年朝廷赐孔庙书物这一史实,更成为连接北宋和今天的一扇窗户,使得今人能一窥那些湮没于岁月长河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