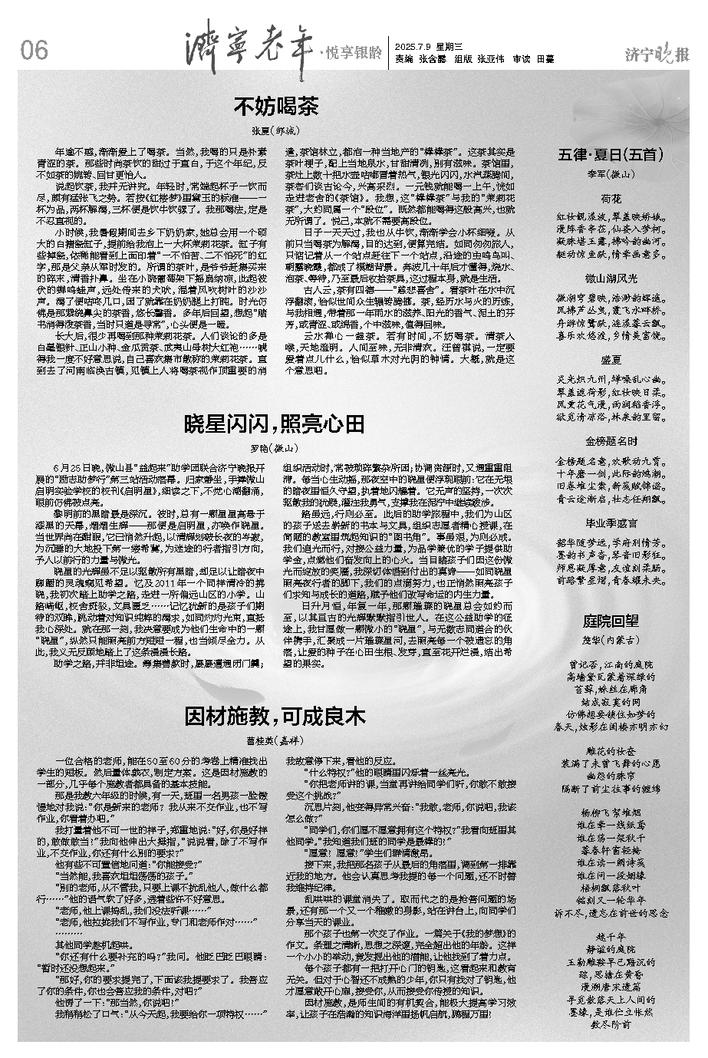张夏(邹城)
年逾不惑,渐渐爱上了喝茶。当然,我喝的只是朴素青涩的茶。那些时尚茶饮的甜过于直白,于这个年纪,反不如茶的婉转、回甘更怡人。
说起饮茶,我并无讲究。年轻时,常端起杯子一饮而尽,颇有猛张飞之势。若按《红楼梦》里黛玉的标准——一杯为品,两杯解渴,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我那喝法,定是不忍直视的。
小时候,我暑假期间去乡下奶奶家,她总会用一个硕大的白搪瓷缸子,提前给我泡上一大杯茉莉花茶。缸子有些掉瓷,依稀能看到上面印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红字,那是父亲从军时发的。所谓的茶叶,是爷爷赶集买来的碎末,清香扑鼻。坐在小院葡萄架下摇扇纳凉,此起彼伏的蝉鸣蛙声,远处传来的犬吠,混着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渴了便咕咚几口,困了就靠在奶奶腿上打盹。时光仿佛是那萦绕鼻尖的茶香,悠长馨香。多年后回望,想起“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心头便是一暖。
长大后,很少再喝到那种茉莉花茶。人们谈论的多是白毫银针、正山小种、金瓜贡茶、武夷山母树大红袍……唬得我一度不好意思说,自己喜欢集市散称的茉莉花茶。直到去了河南临涣古镇,见镇上人将喝茶视作顶重要的消遣,茶馆林立,都泡一种当地产的“棒棒茶”。这茶其实是茶叶梗子,配上当地泉水,甘甜清冽,别有滋味。茶馆里,茶灶上数十把水壶咕嘟冒着热气,银光闪闪,水汽蒸腾间,茶客们谈古论今,兴高采烈。一元钱就能喝一上午,恍如走进老舍的《茶馆》。我想,这“棒棒茶”与我的“茉莉花茶”,大约同属一个“段位”。既然都能喝得这般高兴,也就无所谓了。悦己,本就不需要高段位。
日子一天天过,我也从牛饮,渐渐学会小杯细啜。从前只当喝茶为解渴,目的达到,便算完结。如同匆匆旅人,只惦记着从一个站点赶往下一个站点,沿途的虫鸣鸟叫、朝露晚霞,都成了模糊背景。奔波几十年后才懂得,烧水、泡茶、等待,乃至最后收拾茶具,这过程本身,就是生活。
古人云,茶有四德——“慈悲喜舍”。看茶叶在水中沉浮翻滚,恰似世间众生辗转腾挪。茶,经历水与火的历练,与我相遇,带着那一年雨水的滋养、阳光的香气、泥土的芬芳,或青涩、或绵香,个中滋味,值得回味。
云水禅心一盏茶。若有时间,不妨喝茶。清茶入喉,天地澄明。人间至味,无非清欢。汪曾祺说,一定要爱着点儿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