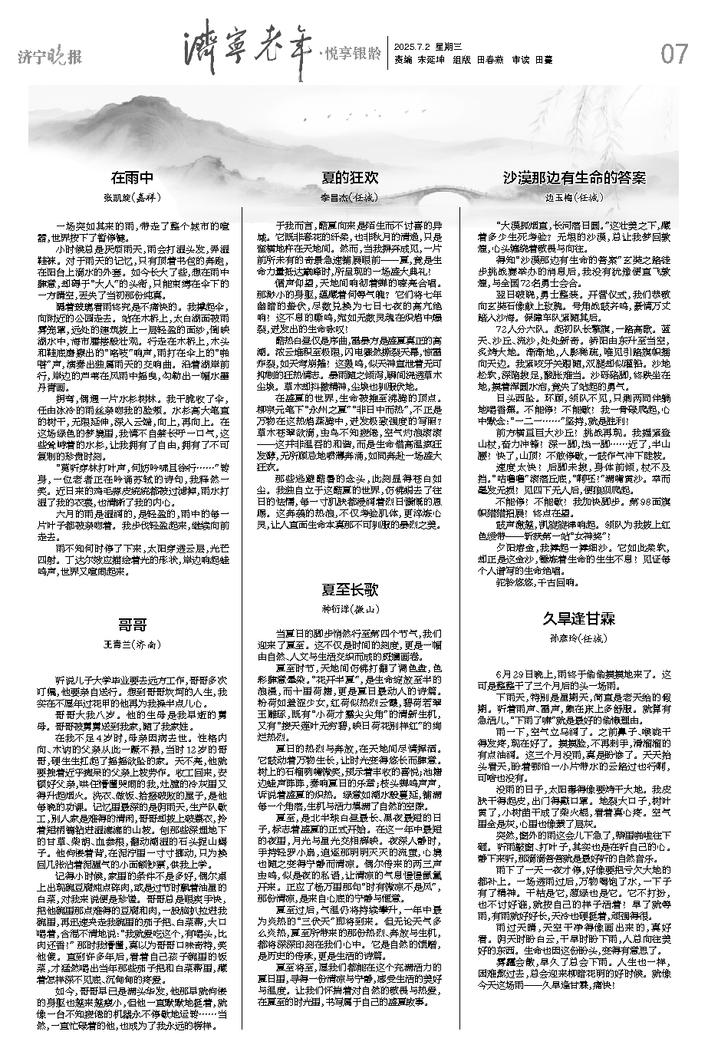王青兰(济南)
听说儿子大学毕业要去远方工作,哥哥多次叮嘱,他要亲自送行。想到哥哥坎坷的人生,我实在不愿年过花甲的他再为我操半点儿心。
哥哥大我八岁。他的生母是我早逝的舅母。哥哥被舅舅送到我家,随了我家姓。
在我不足4岁时,母亲因病去世。性格内向、木讷的父亲从此一蹶不振,当时12岁的哥哥,硬生生扛起了摇摇欲坠的家。天不亮,他就要拽着近乎痴呆的父亲上坡劳作。收工回来,安顿好父亲,哄住懵懂哭闹的我,灶膛的冷灰里又得升起烟火。洗衣、做饭、拾掇破败的屋子,是他每晚的功课。记忆里最深的是阴雨天,生产队歇工,别人家是难得的清闲,哥哥却披上破蓑衣,拎着短柄镐钻进湿漉漉的山坡。刨那些深埋地下的甘草、柴胡、血参根,翻动潮湿的石头捉山蝎子。他佝偻着背,在泥泞里一寸寸挪动,只为换回几张沾着泥腥气的小面额钞票,供我上学。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条件不是多好,偶尔桌上出现碗豆腐炖点碎肉,或是过节时飘着油星的白菜,对我来说便是珍馐。哥哥总是眼疾手快,把他碗里那点难得的豆腐和肉,一股脑扒拉进我碗里,再迅速夹走我碗里的茄子把、白菜帮,大口嚼着,含混不清地说:“我就爱吃这个,有嚼头,比肉还香!” 那时我懵懂,真以为哥哥口味奇特,笑他傻。直到许多年后,看着自己孩子碗里的饭菜,才猛然嚼出当年那些茄子把和白菜帮里,藏着怎样深不见底、沉甸甸的疼爱。
如今,哥哥早已是满头华发,他那早就佝偻的身躯也越来越瘦小,但他一直默默地挺着,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永不停歇地运转……当然,一直忙碌着的他,也成为了我永远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