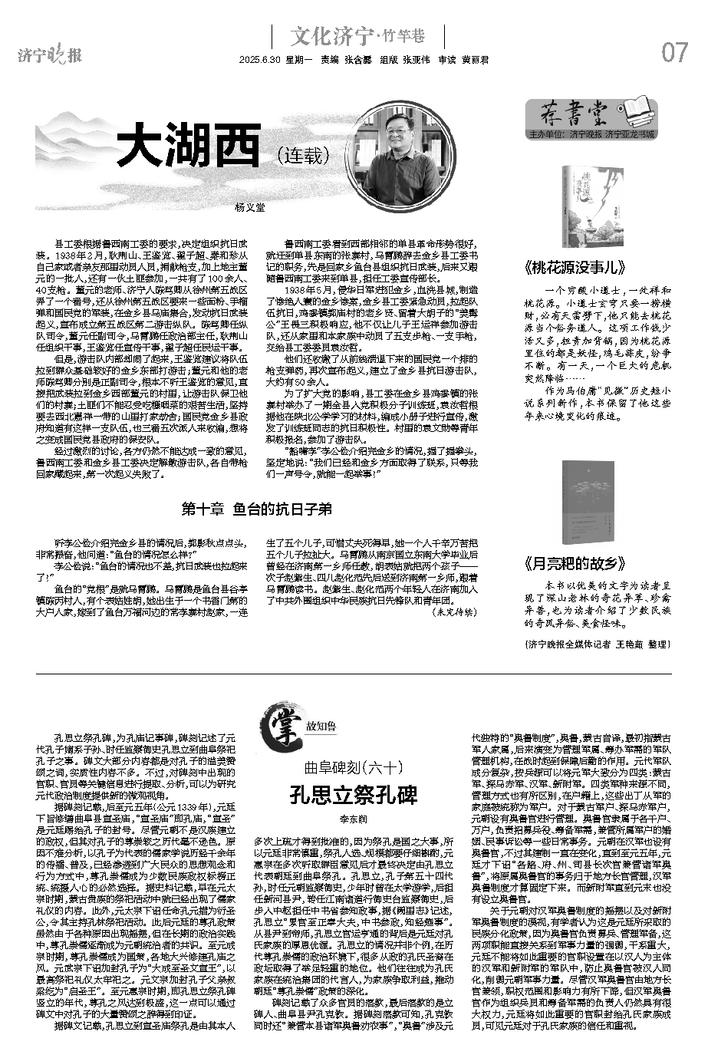李东润
孔思立祭孔碑,为孔庙记事碑,碑刻记述了元代孔子嫡系子孙、时任监察御史孔思立到曲阜祭祀孔子之事。碑文大部分内容都是对孔子的溢美赞颂之词,实质性内容不多。不过,对碑刻中出现的官职、官员等关键信息进行提取、分析,可以为研究元代政治制度提供新的微观视角。
据碑刻记载,后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元廷下旨修缮曲阜县宣圣庙,“宣圣庙”即孔庙,“宣圣”是元廷赐给孔子的封号。尽管元朝不是汉族建立的政权,但其对孔子的尊崇较之历代毫不逊色。原因不难分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历经千余年的传播、普及,已经渗透到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尊孔崇儒成为少数民族政权标榜正统、统摄人心的必然选择。据史料记载,早在元太宗时期,蒙古贵族的祭祀活动中就已经出现了儒家礼仪的内容。此外,元太宗下诏任命孔元措为衍圣公,令其主持孔林祭祀活动。此后元廷的尊孔政策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出现摇摆,但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尊孔崇儒逐渐成为元朝统治者的共识。至元成宗时期,尊孔崇儒成为国策,各地大兴修建孔庙之风。元武宗下诏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以最高祭祀礼仪太牢祀之。元文宗加封孔子父亲叔梁纥为“启圣王”。至元惠宗时期,即孔思立祭孔碑竖立的年代,尊孔之风达到极盛,这一点可以通过碑文中对孔子的大量赞颂之辞得到印证。
据碑文记载,孔思立到宣圣庙祭孔是由其本人多次上疏才得到批准的,因为祭孔是国之大事,所以元廷非常慎重,祭孔人选、规模都要仔细斟酌,元惠宗在多次听取群臣意见后才最终决定由孔思立代表朝廷到曲阜祭孔。孔思立,孔子第五十四代孙,时任元朝监察御史,少年时曾在太学游学,后担任新河县尹,转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后步入中枢担任中书省参知政事,据《阙里志》记述,孔思立“累官至正奉大夫,中书参政,知经筵事”。从县尹到帝师,孔思立官运亨通的背后是元廷对孔氏家族的厚恩优渥。孔思立的情况并非个例,在历代尊孔崇儒的政治环境下,很多从政的孔氏圣裔在政坛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往往成为孔氏家族在统治集团的代言人,为家族争取利益,推动朝廷“尊孔崇儒”政策的深化。
碑刻记载了众多官员的落款,最后落款的是立碑人、曲阜县尹孔克钦。据碑刻落款可知,孔克钦同时还“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奥鲁”涉及元代独特的“奥鲁制度”,奥鲁,蒙古音译,最初指蒙古军人家属,后来演变为管理军属、筹办军需的军队管理机构,在战时起到保障后勤的作用。元代军队成分复杂,按兵源可以将元军大致分为四类: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四类军种来源不同,管理方式也有所区别,在户籍上,这些出丁从军的家庭被统称为军户。对于蒙古军户、探马赤军户,元朝设有奥鲁官进行管理。奥鲁官隶属于各千户、万户,负责招募兵役、筹备军需,兼管所属军户的婚姻、民事诉讼等一些日常事务。元朝在汉军也设有奥鲁官,不过其建制一直在变化,直到至元五年,元廷才下诏“各路、府、州、司县长次官兼管诸军奥鲁”,将原属奥鲁官的事务归于地方长官管理,汉军奥鲁制度才算固定下来。而新附军直到元末也没有设立奥鲁官。
关于元朝对汉军奥鲁制度的摇摆以及对新附军奥鲁制度的漠视,有学者认为这是元廷所采取的民族分化政策,因为奥鲁官负责募兵、管理军备,这两项职能直接关系到军事力量的强弱,干系重大,元廷不能将如此重要的官职设置在以汉人为主体的汉军和新附军的军队中,防止奥鲁官被汉人同化,削弱元朝军事力量。尽管汉军奥鲁官由地方长官兼领,职权范围和影响力有所下降,但汉军奥鲁官作为组织兵员和筹备军需的负责人仍然具有很大权力,元廷将如此重要的官职封给孔氏家族成员,可见元廷对于孔氏家族的信任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