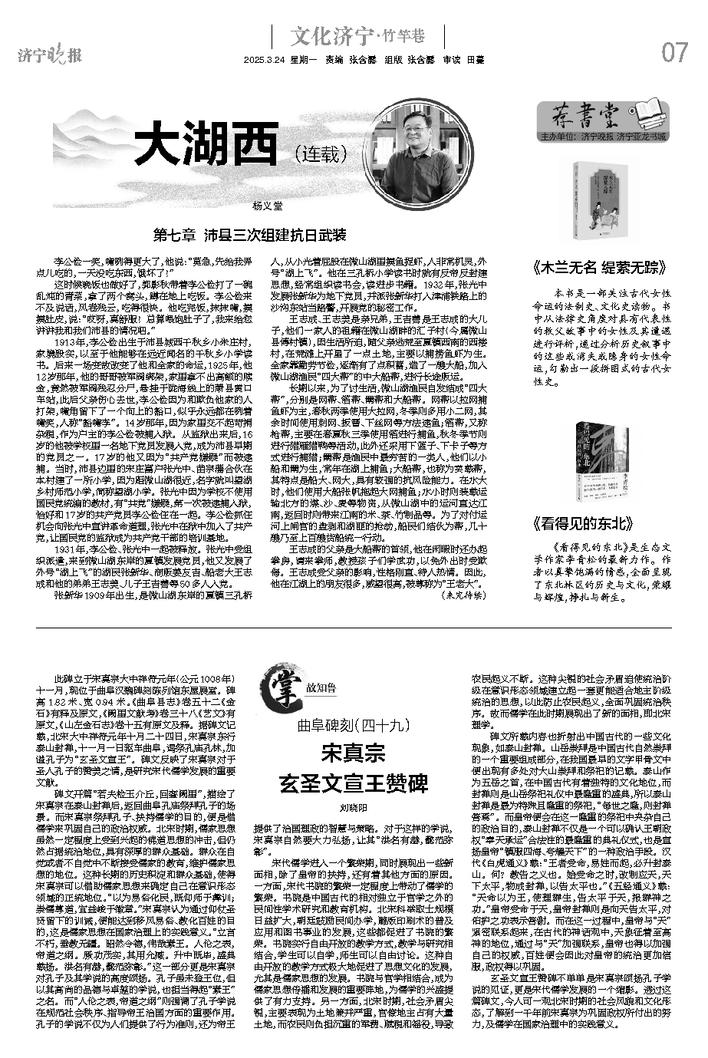刘晓阳
此碑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十一月,现位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东屋展室。碑高 1.82 米、宽 0.94 米。《曲阜县志》卷五十二《金石》有释及原文,《阙里文献考》卷三十八《艺文》有原文,《山左金石志》卷十五有原文及释。据碑文记载,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宋真宗东行泰山封禅,十一月一日驱车曲阜,谒祭孔庙孔林,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碑文反映了宋真宗对于圣人孔子的赞美之情,是研究宋代儒学发展的重要文献。
碑文开篇“若夫检玉介丘,回銮阙里”,描绘了宋真宗在泰山封禅后,返回曲阜孔庙祭拜孔子的场景。而宋真宗祭拜孔子、扶持儒学的目的,便是借儒学来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北宋时期,儒家思想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兴起的佛道思想的冲击,但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群众在自觉或者不自觉中不断接受儒家的教育,维护儒家思想的地位。这种长期的历史积淀和群众基础,使得宋真宗可以借助儒家思想来确定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以为易俗化民,既仰师于彝训;崇儒尊道,宜益峻于徽章。”宋真宗认为通过仰仗圣贤留下的训诫,便能达到移风易俗、教化百姓的目的,这是儒家思想在国家治理上的实践意义。“立言不朽,垂教无疆。昭然令德,伟哉素王。人伦之表,帝道之纲。厥功茂实,其用允臧。升中既毕,盛典载扬。洪名有赫,懿范弥彰。”这一部分更是宋真宗对孔子及其学说的高度颂扬。孔子虽未登王位,但以其高尚的品德与卓越的学说,也担当得起“素王”之名。而“人伦之表,帝道之纲”则强调了孔子学说在规范社会秩序、指导帝王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孔子的学说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行为准则,还为帝王提供了治国理政的智慧与策略。对于这样的学说,宋真宗自然要大力弘扬,让其“洪名有赫,懿范弥彰”。
宋代儒学进入一个繁荣期,同时展现出一些新面相,除了皇帝的扶持,还有着其他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宋代书院的繁荣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儒学的繁荣。书院是中国古代的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朝廷鼓励民间办学,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应用和图书事业的发展,这些都促进了书院的繁荣。书院实行自由开放的教学方式,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学生可以自学,师生可以自由讨论。这种自由开放的教学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发展。书院与官学相结合,成为儒家思想传播和发展的重要阵地,为儒学的兴盛提供了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北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主要表现为土地兼并严重,官僚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则负担沉重的军费、赋税和徭役,导致农民起义不断。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迫使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起一套更能适合地主阶级统治的思想,以此防止农民起义,全面巩固统治秩序。故而儒学在此时期展现出了新的面相,即北宋理学。
碑文所载内容也折射出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如泰山封禅。山岳崇拜是中国古代自然崇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便出现有多处对大山崇拜和祭祀的记载。泰山作为五岳之首,在中国古代有着独特的文化地位,而封禅则是山岳祭祀礼仪中最隆重的盛典,所以泰山封禅是最为特殊且隆重的祭祀,“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而皇帝便会在这一隆重的祭祀中夹杂自己的政治目的,泰山封禅不仅是一个可以确认王朝政权“奉天承运”合法性的最隆重的典礼仪式,也是宣扬皇帝“镇服四海、夸耀天下”的一种政治手段。汉代《白虎通义》载:“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禅,以告太平也。”《五经通义》载:“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皇帝受命于天,皇帝封禅则是向天告太平,对佑护之功表示答谢。而在这一过程中,皇帝与“天”紧密联系起来,在古代的神话观中,天象征着至高神的地位,通过与“天”加强联系,皇帝也得以加强自己的权威,百姓便会因此对皇帝的统治更加信服,政权得以巩固。
玄圣文宣王赞碑不单单是宋真宗颂扬孔子学说的见证,更是宋代儒学发展的一个缩影。透过这篇碑文,今人可一观北宋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文化形态,了解到一千年前宋真宗为巩固政权所付出的努力,及儒学在国家治理中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