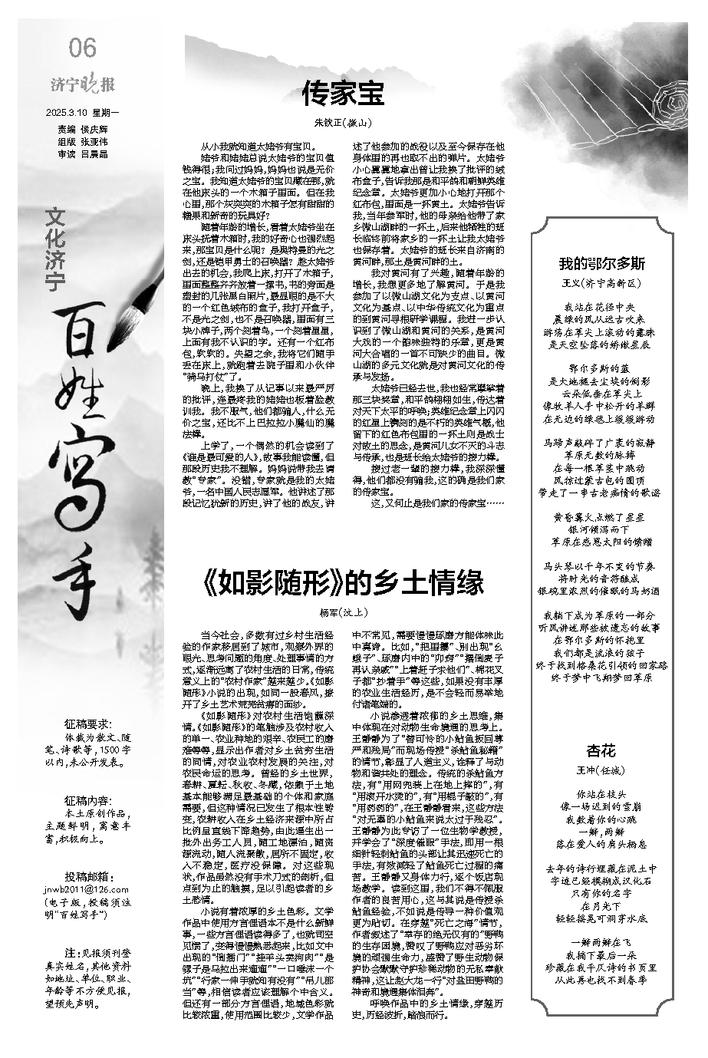杨军(汶上)
当今社会,多数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作家移居到了城市,观察外界的眼光、思考问题的角度、处理事情的方式,逐渐远离了农村生活的日常,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作家”越来越少。《如影随形》小说的出现,如同一股春风,撩开了乡土艺术荒芜贫瘠的面纱。
《如影随形》对农村生活饱蘸深情。《如影随形》的笔触涉及农村收入的单一、农业种地的艰辛、农民工的磨难等等,显示出作者对乡土贫穷生活的同情,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关注,对农民命运的思考。曾经的乡土世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依赖于土地基本能够满足最基础的个体和家庭需要,但这种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农耕收入在乡土经济来源中所占比例呈直线下降趋势,由此逼生出一批外出务工人员,随工地漂泊,随资源流动,随人流聚散,居所不固定,收入不稳定,医疗没保障。对这些现状,作品虽然没有手术刀式的剖析,但点到为止的触摸,足以引起读者的乡土愁情。
小说有着浓厚的乡土色彩。文学作品中使用方言俚语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些方言俚语读得多了,也就司空见惯了,变得慢慢熟悉起来,比如文中出现的“倒插门”“挂羊头卖狗肉”“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一口唾沫一个坑”“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吊儿郎当”等,相信读者应该理解个中含义。但还有一部分方言俚语,地域色彩就比较浓重,使用范围比较少,文学作品中不常见,需要慢慢琢磨方能体味此中真谛。比如,“把里攥”、别出现“幺蛾子”、琢磨内中的“卯窍”“撂倒麦子再认亲戚”“上着赶子求他们”、棉花叉子都“抄着手”等这些,如果没有丰厚的农业生活经历,是不会轻而易举地付诸笔端的。
小说渗透着浓郁的乡土思维,集中体现在对动物生命境遇的思考上。王静静为了“替可怜的小鲇鱼扳回尊严和残局”而现场传授“杀鲇鱼秘籍”的情节,彰显了人道主义,诠释了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理念。传统的杀鲇鱼方法,有“用网兜装上在地上摔的”,有“用滚开水烫的”,有“用棍子敲的”,有“用药药的”,在王静静看来,这些方法“对无辜的小鲇鱼来说太过于残忍”。王静静为此专访了一位生物学教授,并学会了“深度催眠”手法,即用一根细针轻刺鲇鱼的头部让其迅速死亡的手法,有效减轻了鲇鱼死亡过程的痛苦。王静静又身体力行,逐个饭店现场教学。读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的良苦用心,这与其说是传授杀鲇鱼经验,不如说是传导一种价值观更为贴切。在穿越“死亡之海”情节,作者叙述了“幸存的绝无仅有的”野鸭的生存困境,赞叹了野鸭应对恶劣环境的顽强生命力,盛赞了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默默守护珍稀动物的无私奉献精神,这让赵大龙一行“对盐田野鸭的神奇和境遇集体泪奔”。
呼唤作品中的乡土情缘,穿越历史,历经波折,踏浪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