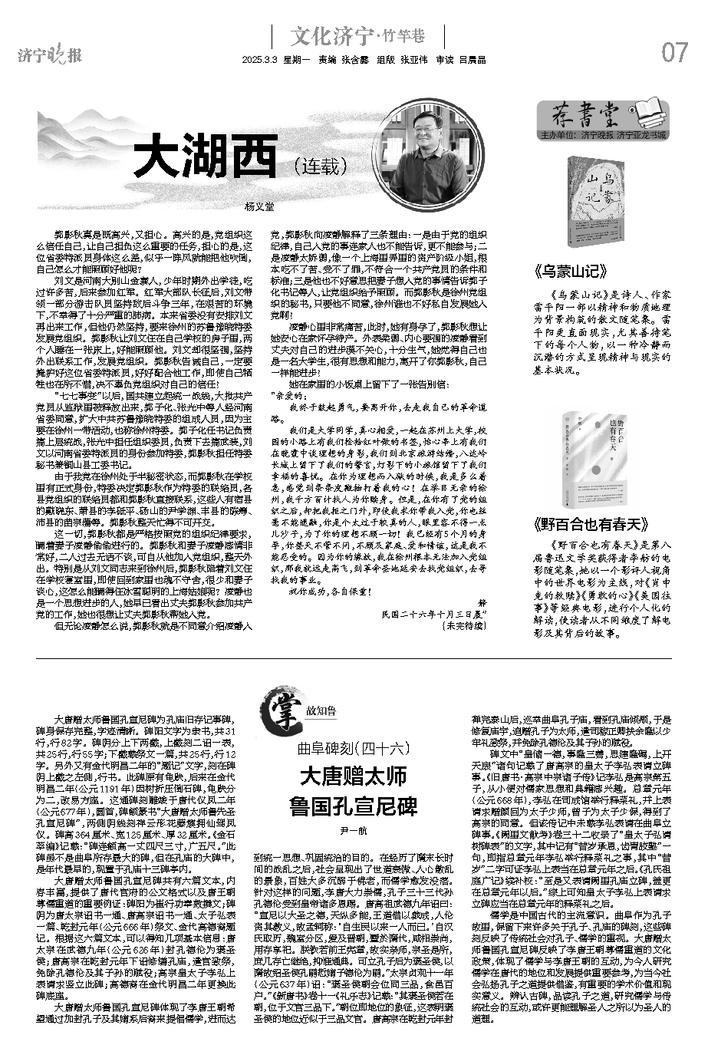尹一航
大唐赠太师鲁国孔宣尼碑为孔庙旧存记事碑,碑身保存完整,字迹清晰。碑阳文字为隶书,共31行,行82字。碑阴分上下两截,上截刻二诏一表,共25行,行55字;下截载祭文一篇,共25行,行12字。另外又有金代明昌二年的“题记”文字,刻在碑阴上截之左侧,行书。此碑原有龟趺,后来在金代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因树折压倒石碑,龟趺分为二,改易方座。这通碑刻雕竣于唐代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圆首,碑额篆书“大唐赠太师鲁先圣孔宣尼碑”,两侧阴线刻祥云形花藤簇拥仙驾凤仪。碑高364厘米、宽125厘米、厚32厘米。《金石萃编》记载:“碑连额高一丈四尺三寸,广五尺。”此碑虽不是曲阜所存最大的碑,但在孔庙的大碑中,是年代最早的,现置于孔庙十三碑亭内。
大唐赠太师鲁国孔宣尼碑共有六篇文本,内容丰富,提供了唐代官府的公文格式以及唐王朝尊儒重道的重要例证:碑阳为崔行功奉敕撰文;碑阴为唐太宗诏书一通、唐高宗诏书一通、太子弘表一篇、乾封元年(公元666年)祭文、金代高德裔题记。根据这六篇文本,可以得知几项基本信息:唐太宗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封孔德伦为褒圣侯;唐高宗在乾封元年下诏修缮孔庙,遣官致祭,免除孔德伦及其子孙的赋役;高宗皇太子李弘上表请求竖立此碑;高德裔在金代明昌二年更换此碑底座。
大唐赠太师鲁国孔宣尼碑体现了李唐王朝希望通过加封孔子及其嫡系后裔来提倡儒学,进而达到统一思想、巩固统治的目的。在经历了隋末长时间的战乱之后,社会呈现出了世道衰微、人心散乱的景象,百姓大多沉溺于佛老,而儒学愈发没落。针对这样的问题,李唐大力崇儒,孔子三十三代孙孔德伦受到皇帝诸多恩赐。唐高祖武德九年诏曰:“宣尼以大圣之德,天纵多能,王道借以裁成,人伦资其教义,故孟轲称:‘自生民以来一人而已。’自汉氏取历,魏室分区,爱及晋朝,暨於隋代,咸相崇尚,用存享祀。朕钦若前王宪章,故实亲师,宗圣是所,庶几存亡继绝,抑惟通典。可立孔子后为褒圣侯,以隋故绍圣侯孔嗣悊嫡子德伦为嗣。”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诏:“褒圣侯朝会位同三品,食邑百户。”《新唐书》卷十一《礼乐志》记载:“其褒圣侯若在朝,位于文官三品下。”朝位即地位的象征,这表明褒圣侯的地位近似于三品文官。唐高宗在乾封元年封禅完泰山后,巡幸曲阜孔子庙,看到孔庙倾颓,于是修复庙宇,追赠孔子为太师,遣司稼正卿扶余隆以少牢礼致祭,并免除孔德伦及其子孙的赋役。
碑文中“皇储一德,事隆三善,思建隆碣,上开天扆”诸句记载了唐高宗的皇太子李弘表请立碑事。《旧唐书·高宗中宗诸子传》记李弘是高宗第五子,从小便对儒家思想和典籍感兴趣。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弘在司成馆举行释菜礼,并上表请求赠颜回为太子少师,曾子为太子少保,得到了高宗的同意。但该传记中未载李弘表请在曲阜立碑事。《阙里文献考》卷三十二收录了“皇太子弘请树碑表”的文字,其中记有“昔岁承恩,齿胄胶塾”一句,即指总章元年李弘举行释菜礼之事,其中“昔岁”二字可证李弘上表当在总章元年之后。《孔氏祖庭广记》续补校:“至是又表请阙里孔庙立碑,盖更在总章元年以后。”综上可知皇太子李弘上表请求立碑应当在总章元年的释菜礼之后。
儒学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曲阜作为孔子故里,保留下来许多关于孔子、孔庙的碑刻,这些碑刻反映了传统社会对孔子、儒学的重视。大唐赠太师鲁国孔宣尼碑反映了李唐王朝尊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体现了儒学与李唐王朝的互动,为今人研究儒学在唐代的地位和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为当今社会弘扬孔子之道提供借鉴,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辨认古碑,品读孔子之道,研究儒学与传统社会的互动,或许更能理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