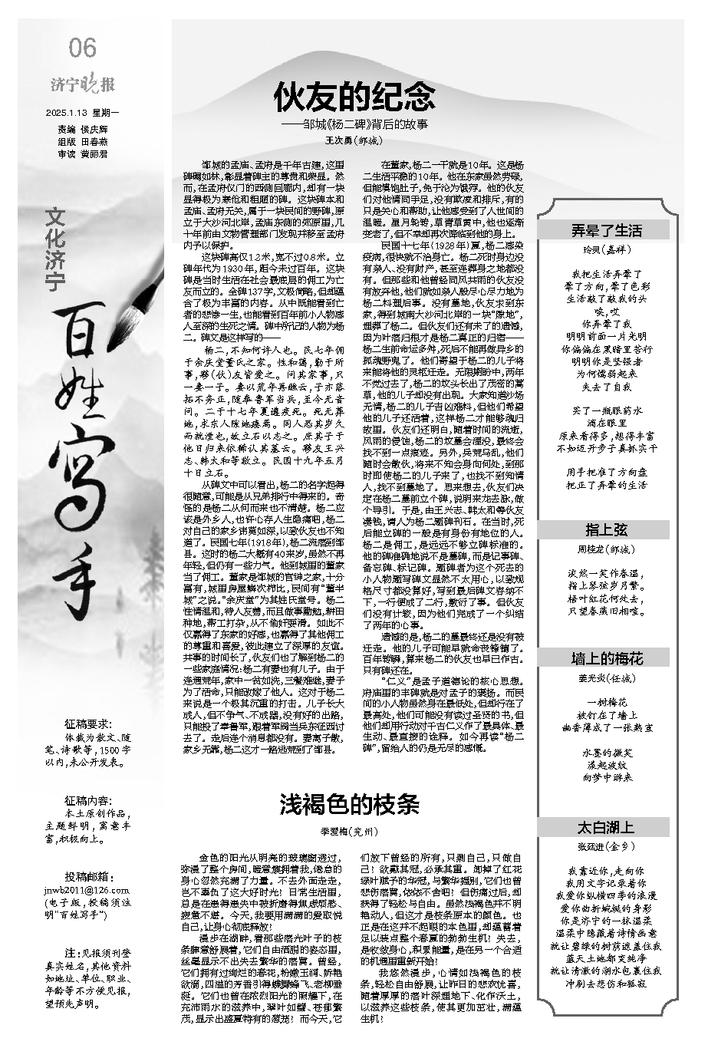王次勇(邹城)
邹城的孟庙、孟府是千年古建,这里碑碣如林,彰显着碑主的尊贵和荣显。然而,在孟府仪门的西侧回廊内,却有一块显得极为寒伧和粗陋的碑。这块碑本和孟庙、孟府无关,属于一块民间的野碑,原立于大沙河北岸,孟庙东侧的郊原里,几十年前由文物管理部门发现并移至孟府内予以保护。
这块碑高仅1.2米,宽不过0.8米。立碑年代为1930年,距今未过百年。这块碑是当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佣工为亡友而立的。全碑137字,文极简略,但却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从中既能看到亡者的悲惨一生,也能看到百年前小人物感人至深的生死之情。碑中所记的人物为杨二。碑文是这样写的——
杨二,不知何许人也。民七年佣于余庆堂董氏之家。性和蔼,勤于所事,夥(伙)友皆爱之。问其家事,只一妻一子。妻以荒年再醮云,子亦落拓不务正,随奉鲁军当兵,至今无音问。二于十七年夏遘疫死。死无葬地,求东人隙地瘗焉。同人恐其岁久而就湮也,故立石以志之。庶其子于他日归来依稀认其墓云。夥友王兴志、韩太和等敬立。民国十九年五月十日立石。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杨二的名字起得很随意,可能是从兄弟排行中得来的。奇怪的是杨二从何而来也不清楚。杨二应该是外乡人,也许心存人生隐痛吧,杨二对自己的家乡讳莫如深,以致伙友也不知道了。民国七年(1918年),杨二流落到邹县。这时的杨二大概有40来岁,虽然不再年轻,但仍有一些力气。他到城里的董家当了佣工。董家是邹城的官绅之家,十分富有,城里房屋鳞次栉比,民间有“董半城”之说。“余庆堂”为其姓氏堂号。杨二性情温和,待人友善,而且做事勤勉,耕田种地,帮工打杂,从不偷奸耍滑。如此不仅赢得了东家的好感,也赢得了其他佣工的尊重和喜爱,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共事的时间长了,伙友们也了解到杨二的一些家庭情况:杨二有妻也有儿子。由于连遇荒年,家中一贫如洗,三餐难继,妻子为了活命,只能改嫁了他人。这对于杨二来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儿子长大成人,但不争气、不成器,没有好的出路,只能投了奉鲁军,跟着军阀当兵东征西讨去了。走后连个消息都没有。妻离子散,家乡无靠,杨二这才一路逃荒到了邹县。
在董家,杨二一干就是10年。这是杨二生活平稳的10年。他在东家虽然劳碌,但能填饱肚子,免于沦为饿殍。他的伙友们对他情同手足,没有欺凌和排斥,有的只是关心和帮助,让他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星月轮转,草青草黄中,他也逐渐变老了,但不幸却再次降临到他的身上。
民国十七年(1928年)夏,杨二感染疫病,很快就不治身亡。杨二死时身边没有亲人、没有财产,甚至连葬身之地都没有。但那些和他曾经同风共雨的伙友没有放弃他,他们就如亲人般尽心尽力地为杨二料理后事。没有墓地,伙友求到东家,得到城南大沙河北岸的一块“隙地”,埋葬了杨二。但伙友们还有未了的遗憾,因为叶落归根才是杨二真正的归宿——杨二生前命运多舛,死后不能再做异乡的孤魂野鬼了。他们寄望于杨二的儿子将来能将他的灵柩迁走。无限期盼中,两年不觉过去了,杨二的坟头长出了茂密的蒿草,他的儿子却没有出现。大家知道沙场无情,杨二的儿子吉凶难料,但他们希望他的儿子还活着,这样杨二才能够魂归故里。伙友们还明白,随着时间的流逝,风雨的侵蚀,杨二的坟墓会湮没,最终会找不到一点痕迹。另外,兵荒马乱,他们随时会散伙,将来不知会身向何处,到那时即使杨二的儿子来了,也找不到知情人,找不到墓地了。思来想去,伙友们决定在杨二墓前立个碑,说明来龙去脉,做个导引。于是,由王兴志、韩太和等伙友凑钱,请人为杨二题碑刊石。在当时,死后能立碑的一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杨二是佣工,是远远不够立碑标准的。他的碑准确地说不是墓碑,而是记事碑、备忘碑、标记碑。题碑者为这个死去的小人物题写碑文显然不太用心,以致规格尺寸都没算好,写到最后碑文容纳不下,一行便成了二行,敷衍了事。但伙友们没有计较,因为他们完成了一个纠结了两年的心事。
遗憾的是,杨二的墓最终还是没有被迁走。他的儿子可能早就命丧锋镝了。百年转瞬,算来杨二的伙友也早已作古。只有碑还在。
“仁义”是孟子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府庙里的丰碑就是对孟子的褒扬。而民间的小人物虽然身在最低处,但却行在了最高处,他们可能没有读过圣贤的书,但他们却用行动对千古仁义作了最具体、最生动、最直接的诠释。如今再读“杨二碑”,留给人的仍是无尽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