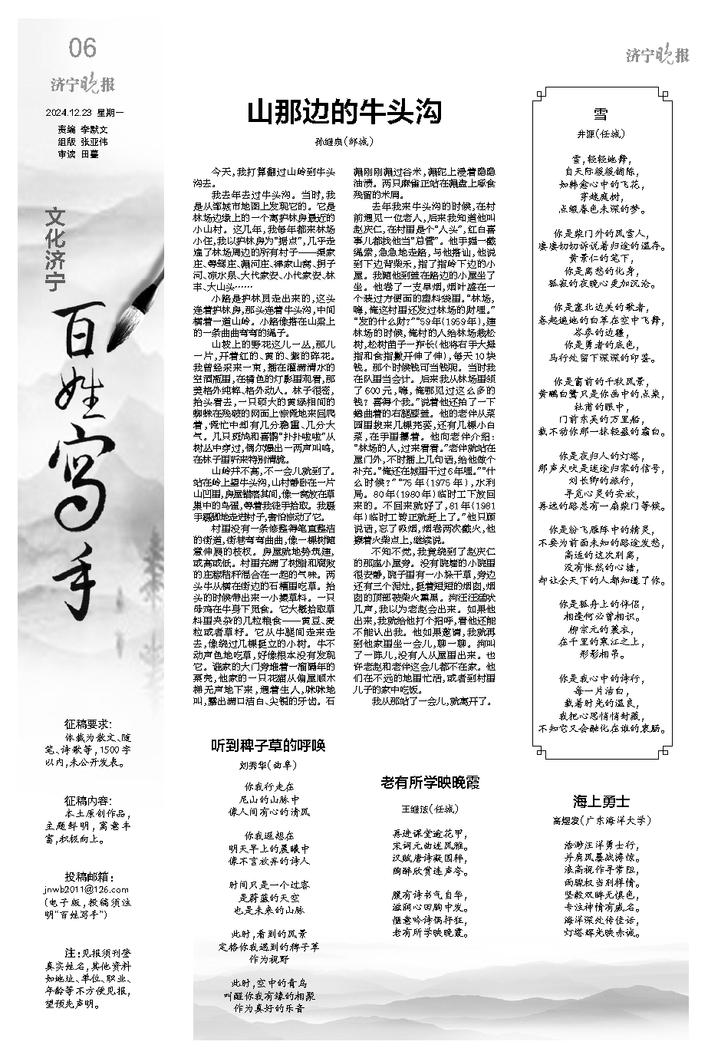孙继泉(邹城)
今天,我打算翻过山岭到牛头沟去。
我去年去过牛头沟。当时,我是从邹城市地图上发现它的。它是林场边缘上的一个离护林房最近的小山村。这几年,我每年都来林场小住,我以护林房为“据点”,几乎走遍了林场周边的所有村子——渠家庄、等驾庄、碾河庄、律家山窝、拐子河、凉水泉、大代家安、小代家安、林丰、大山头……
小路是护林员走出来的,这头连着护林房,那头连着牛头沟,中间横着一道山岭。小路像搭在山梁上的一条曲曲弯弯的绳子。
山坡上的野花这儿一丛,那儿一片,开着红的、黄的、紫的碎花。我曾经采来一束,插在灌满清水的空酒瓶里,在橘色的灯影里观看,那美格外纯粹、格外动人。林子很密,抬头看去,一只硕大的黄绿相间的蜘蛛在残破的网面上惊慌地来回爬着,慌忙中却有几分稳重、几分大气。几只斑鸠和喜鹊“扑扑啦啦”从树丛中穿过,偶尔爆出一两声叫鸣,在林子里听来特别清脆。
山岭并不高,不一会儿就到了。站在岭上望牛头沟,山村静卧在一片山凹里,房屋错落其间,像一窝放在草巢中的鸟蛋,等着我徒手拾取。我蹑手蹑脚地走进村子,害怕惊动了它。
村里没有一条修整得笔直整洁的街道,街巷弯弯曲曲,像一棵树随意伸展的枝杈。房屋就地势筑建,或高或低。村里充满了树脂和腐败的庄稼秸秆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两头牛从横在街边的石槽里吃草。抬头的时候带出来一小撮草料。一只母鸡在牛身下觅食。它大概拾取草料里夹杂的几粒粮食——黄豆、麦粒或者草籽。它从牛腿间走来走去,像绕过几棵挺立的小树。牛不动声色地吃草,好像根本没有发现它。谁家的大门旁堆着一溜隔年的栗壳,他家的一只花猫从偏屋顺木梯无声地下来,遇着生人,咪咪地叫,露出满口洁白、尖锐的牙齿。石碾刚刚碾过谷米,碾砣上浸着隐隐油渍。两只麻雀正站在碾盘上啄食残留的米屑。
去年我来牛头沟的时候,在村前遇见一位老人,后来我知道他叫赵庆仁,在村里是个“人头”,红白喜事儿都找他当“总管”。他手握一截绳索,急急地走路,与他搭讪,他说到下边背柴禾,指了指岭下边的小屋。我随他到盖在路边的小屋坐了坐。他卷了一支旱烟,烟叶盛在一个装过方便面的塑料袋里。“林场,嗨,俺这村里还发过林场的财哩。”“发的什么财?”“59年(1959年),建林场的时候,俺村的人给林场栽松树,松树苗子一拃长(他将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撇开伸了伸),每天10块钱。那个时候钱可当钱呢。当时我在队里当会计。后来我从林场里领了600元,嗨,俺哪见过这么多的钱?喜得个我。”说着他还拍了一下蜷曲着的右腿膝盖。他的老伴从菜园里拔来几棵芫荽,还有几棵小白菜,在手里攥着。他向老伴介绍:“林场的人,过来看看。”老伴就站在屋门外,不时插上几句话,给他做个补充。“俺还在城里干过6年哩。”“什么时候?”“75年(1975年),水利局。80年(1980年)临时工下放回来的。不回来就好了,81年(1981年)临时工转正就赶上了。”他只顾说话,忘了吸烟,烟卷两次截火,他擦着火柴点上,继续说。
不知不觉,我竟绕到了赵庆仁的那座小屋旁。没有院墙的小院里很安静,院子里有一小垛干草,旁边还有三个泥灶,挺着短短的烟囱,烟囱的顶部被柴火熏黑。狗汪汪猛吠几声,我以为老赵会出来。如果他出来,我就给他打个招呼,看他还能不能认出我。他如果邀请,我就再到他家里坐一会儿,聊一聊。狗叫了一阵儿,没有人从屋里出来。也许老赵和老伴这会儿都不在家。他们在不远的地里忙活,或者到村里儿子的家中吃饭。
我从那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