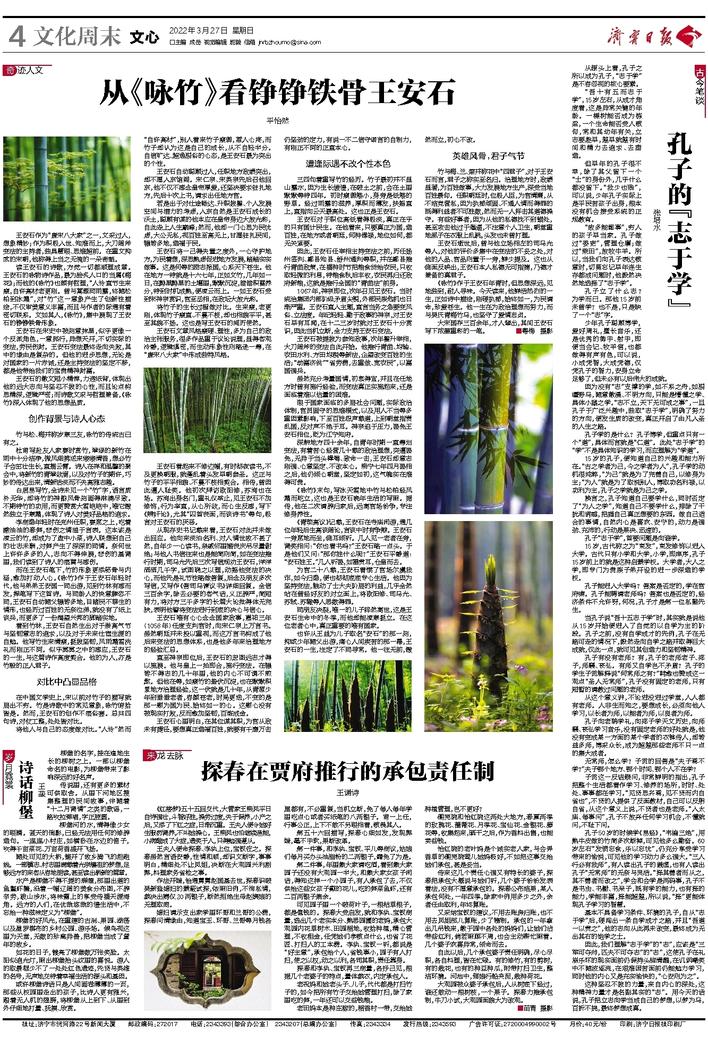从源头上看,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志于学”是不容忽视的核心要素。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15岁左右,从成才角度看,这是异常关键的年龄。一棵树能否成为栋梁,一个生命能否受人敬仰,常和其幼年有关,立志要趁早,越早就越有时间和精力去追求、去塑造。
但早年的孔子很不幸,除了其父留下一个“士”的身份外,几乎什么都没留下。“我少也贱”,可以说,少年孔子实际上是平民苦孩子出身,根本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
“故多能鄙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孔子做过“委吏”,管理仓廪;做过“乘田”,放牧牛羊。所以,当我们向孔子表达敬意时,切莫忘记早年连生存都成问题时,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志于学”。
孔子立了什么志?为学而已。那他15岁前未曾学?也不是,只是缺了一个“志”字。
少年孔子聪颖博学,爱好周礼,擅长音乐,还是优秀的御手、射手,即便当会记、牧羊倌,也都做得有声有色,可以说,小成凭智,大成凭德,仅凭孔子的智力,安身立命足够了,但未必有以后伟大的成就。
因为没有“志”支撑的学,如不系之舟,如脱缰野马,随意散漫、不明方向,只能是懵懂之学、具体小器之学。“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一旦孔子于广泛兴趣中,独取“志于学”,明确了努力的方向,便发生质的改变,真正开启了由凡入圣的人生之路。
孔子学的是什么?孔子博学,但重点只有一个“道”,具体而言就是“仁道”。此处“志于学”的“学”不是具体知识的学习,而应理解为“学道”。
15岁的孔子,便知道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所在。“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学的动机很纯粹,“为己”就是为了完善自己,以修身为主;“为人”就是为了取悦别人,博取功名利禄,以功利为主,孔子之学就是为己之学。
换言之,孔子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同时否定了“为人之学”,知道自己不要学什么,排除了干扰和诱惑,把握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做自己适合的事情,自然内心是喜欢、安宁的,动力是强劲、充沛的,行动是果决、迅速的。
孔子“志于学”,首要问题是向谁学。
15岁,古代称之为“束发”,束发修饰以进入大学。古代只有小学和大学,小学,即庠序,孔子15岁前上的就是这种启蒙学校。大学者,大人之学,即专门为贵族子弟开设的进一步深造的学校。
孔子能进入大学吗?答案是否定的,学在官府嘛。孔子能聘请老师吗?答案也是否定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呀,何况,孔子才是第一位私塾先生。
当孔子说“吾十五志于学”时,其实就是说他从15岁开始便进入了自觉的以自学为主的阶段。孔子之前,没有自学成才的先例,孔子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毅然走向自学之路并取得巨大成就,仅此一点,就可见其创造力和坚韧精神。
孔子有没有老师?有,孔子的老师老子、郯子,师襄、苌弘。有师又自学岂不矛盾?孔子的学生子贡解释说“何常师之有?”韩愈也赞成这一观点“圣人无常师”,孔子没有固定的老师,只有短暂的请教过问题的老师。
从这个意义讲,不论进没进过学堂,人人都有老师。人非生而知之,要想成长,必须向他人学习,以长者为师,以能者为师,以良者为师。
孔子向老聃学礼,向郯子学天文历史,向师襄、苌弘学习音乐,没有固定老师的好处就是,他没有变成某一方面的某个学者的衣钵传人,却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成为超越那些老师不只一点的集大成者。
无常师,怎么学?子贡的回答是“夫子焉不学?”夫子哪个地方、哪个时间、哪个人不在学?
子贡这一反诘疑问,非常鲜明的指出,孔子把整个生活都看作学习、修养的场所,时时、处处、事事都在学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不贤的人提供了反面教材,自己可以反躬自省,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贤者也是老师。“入太庙、每事问”,孔子不放弃任何学习机会,不懂就问,不耻下问。
孔子50岁的时候学《易经》,“韦编三绝”,用熟牛皮做的竹简多次断掉,可见他多么勤奋。60岁左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仍充分享受学习带来的愉悦,可见他的学习动力多么强大。“三人行必有我师”,有人读出孔子的谦虚,也有人读出孔子“无常师”的无奈与灵活。“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学会和会学是两码事,孔子不是书虫、书橱、书呆子,既有学的能力,也有择的能力,学能丰富,择能超越,所以说,“择”更能体现孔子学习的智慧。
基本不具备学习条件、环境的孔子,自从“志于学”后,硬闯出一条自学成才之路,并且“吾道一以贯之”,他的志向从此再未改变,最终成为无出其右的饱学之士。
因此,我们理解“志于学”的“志”,应该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使孔子在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仍保持头脑清醒,在讥讽嘲笑中不随波逐流,在艰难困苦面前仍能勉力学习,同时他的内心又是充实愉快的,“心安则为之”。
这种坚忍不拔的力量,来自内心的深处,这种精神力量才是名副其实的“志”。用今天的话说,孔子把立志向学当成自己的梦想,以梦为马,百折不挠,最终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