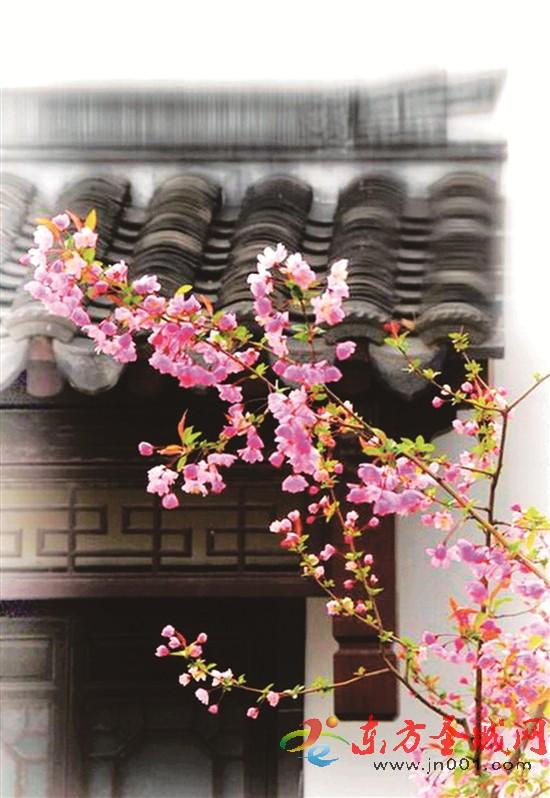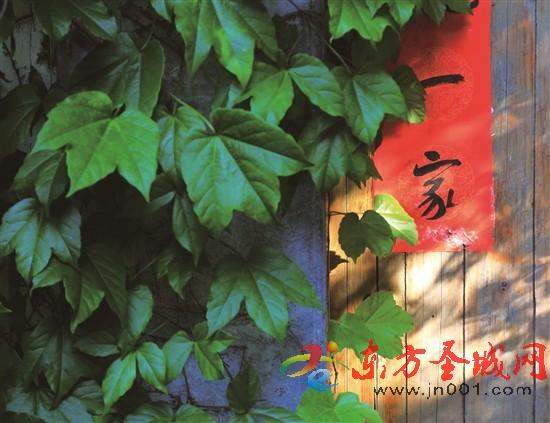2021年初夏,经过几次约访,记者终于在韩爱臣家里与她见面了。眼前的这位老人,既和蔼又朴实。而一天的采访过后,让记者感动的则是她的友善、敬业、勤俭、包容,是她给孩子们的良好家教,给家庭营建的淳朴家风。
吃亏包憨苦累别嫌,人这样才能立体面
1947年,韩爱臣出生在现今的嘉祥县梁宝寺镇湖连井村。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贫穷是中国的基本面貌,何况在落后的农村。韩爱臣祖辈都是农民,父辈兄弟四个,父亲排行老三,她却是同辈人中第一个幸存下来的孩子。由于条件落后、生活艰难,在她之前,伯伯叔叔家出生的孩子,尽数夭折,竟无一成活。这样的家庭境遇,便让家人对她的出生充满惊喜,也满怀期待。
在后来的日子里,韩爱臣也确实在天地保佑之中,亲人呵护之下,得以幸存,并且健康成长。
一些温馨的生活场景,她至今历历在目。终生信佛的奶奶,将她放在膝上,或为她说书,或给她诵经。她安静地坐着,倾心地聆听,虽然似懂非懂,甚至根本不懂,但奶奶念经的模样,慈祥而虔诚,让她心安,也让她神往。
对韩爱臣影响最大的人,当然也是奶奶。老人家质朴的语言里,常会带着有益的教诲和人生的禅意。比如“心里不明,不能点灯”“嘴甜心苦,念得什么经”“上山的兔子,别笑下山的虎” “人到难处拉一把,心到苦处别添盐”等等。
她熟记于心,先用来约束自己,再用来教导儿子,后来又传给孙辈,用好的传统,引领家人向真向善向美向好。
韩爱臣知书达礼,其实她并没正式上过学,所谓“两年”的学业,还是“顶替”妹妹学来的。小时候,刚上二年级的妹妹,因为年幼瘦小,常受同位欺负,说啥也不愿上学了。韩爱臣闻听此事,便对妹妹说:“你不愿上学,我替你去上。”那时韩爱臣已是9岁,听话又懂事儿,便高兴地来到学校。只是妹妹已读到二年级,班里的学习内容与进度,自然不会照顾她重学,好在小爱臣心灵聪慧,记忆力强,刻苦用功,经过老师补课辅导,很快赶了上来,学的课文至今还能背诵。
人算终究不如天算。一年半后,韩爱臣的学业,便因一场天灾戛然而止。1957年汛期,济宁发生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整个地区全泡在水中。七月,老天连续降雨,因雨量过度集中,水量超过了湖河的容泄能力,水位陡增造成湖河决口。七月下旬,湖西大小河流堤坝漫溢或溃决,金乡、嘉祥、济宁等地纵横二三百里一片汪洋,到处可以行舟。
这次洪灾以湖滨和湖西平原地区灾情最重,水深一般1米至2米,时间长且排泄慢,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大灾之后,大难随至。1958年“大跃进”,虚报浮夸盛行;1959年至1961年,国家又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此时韩家已穷得揭不开锅,韩爱臣的“求学梦”彻底破灭,跟着大人逃荒要饭去了。
苦难作为人生的另一所“学校”,不由分说地将韩爱臣“录取”进来,她只好像高尔基那样在困苦中读“我的大学”了。在外出逃荒的时光,她跟着大人,在肥城、宁阳和阳谷及周围一带,饱尝人间凄苦,白天吃人家残羹剩饭,晚上住人家的厨屋,有时甚至住旧庙破窑。
虽然苦到极处,但有时也让她体会到人间真情。一些好心人家,见韩爱臣聪明伶俐,口甜腿勤,可爱可怜,也会给一些米和面,她便高兴地道谢,然后带回来,交给家人做饭。三年灾荒终于过去,一家人得以幸存。
韩爱臣感慨:“人在无时给一口,胜过有时给一斗。”在艰难的岁月里,好心人的接济和恩施,是她一生难忘的温暖。
一场大灾终于过去了,日子虽然仍是艰苦,但总是强过逃荒要饭。韩爱臣说,穷没根,富没苗,人要有志气。她渐渐长大,懂事知理,在15岁那年,她被选为村里的第一个“保健员”,也就是后来的赤脚医生。
韩爱臣边做保健工作,边学习文化,不到一年,全村人的姓名,都能会认会记,工作无一差错。16岁那年,村里兴办民校,她第一个报名参加,学习用功,进步很快,学过的课文,距今五十多年了,仍能背诵。如“黄继光,杀敌猛。为祖国,立大功。董存瑞,是英雄,炸碉堡,献生命。刘胡兰,骨头硬,生伟大,死光荣”“脱便衣,穿军装,新式步枪肩上扛。雄赳赳,气昂昂,架枪备炮守国防,美帝国主义太疯狂……”这些课文至今熟记在心,让人为之敬佩。
1963年,韩爱臣成了村里第一个共青团员,还是公社第一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19岁时,梁宝寺公社大礼堂举办背诵比赛,她登台背诵“老三篇”,赢得满堂彩。这事距今近六十年了,现在的韩爱臣对有些段落仍熟记在心。
那时的农村条件苦,韩爱臣却生活得充实而快乐。慈祥的奶奶,勤劳的父亲,好心的近门嫂子,都用良言善行影响着她。在社会这所“大学”里,身边的好人就是“名师”,她接受着最接地气的教育。
农活、家务活,她都会干。插稻子橫竖一条线,割麦子总是打前站;纺线织布、插花描红这类技术活,她也是行家里手。村里稍有些技术难度的活儿,都是先派她外出学习,学成归来传授给众乡亲。
韩爱臣结婚后,在村里当赤脚医生, 从来都是有求必应,随叫随到,及时施救,没要过任何报酬,甚至在寒冷的冬天,为别人接生完,连一碗红糖水都没喝过人家的。
那时,村里流传这样的民谣:“疟疾蚊子传,吃药不要钱;得了疟疾病,去找保健员”。这是对党的基层卫生工作的赞颂,也是对韩爱臣的赞美。
1975年,经过学习培训,韩爱臣以临时工身份进入大张楼镇医院工作。有一次,因为工作太忙,晚上九点多钟回到家,二儿子还没回来,她赶紧拿起手电筒去找,发现他在村外地瓜垄沟里睡着了。韩爱臣在镇医院七年,工作从无半点儿差错,态度好、业务精,广受患者和家属们好评。
韩爱臣说,为人处世,要做实在人,能吃亏包憨,苦累别嫌,这样才能立体面;做人要将心比心,做事要设身处地。公公婆婆咽气时,都是韩爱臣带领家人为二老穿衣服。哥哥在农村,弟弟工资低,她给丈夫提出来,二老的丧葬费全由自家包了,不让哥弟出分文钱。老人出殡后,亲戚送的礼品,先让哥嫂、弟媳挑,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她回娘家,从自家拿去的都是不值钱的东西;她去婆家,都是拿值钱的东西。婆婆在世的时候对别人说:“俺这个儿媳真好,百里不挑一”。
几十年里,韩爱臣在婆媳、妯娌、夫妻、母子甚至邻里之间,从来没生过气吵过架。 公公婆婆、父亲母亲在她照料下,人人得以善终。婆婆更是寿至九十以上,老人临终前,韩爱臣更是一夜不敢合眼,照顾着婆婆,心里头关心着家里其他人,让他们轮着休息,自己始终不离老人的床边。
韩爱臣说:“人的名,树的影。邻里百舍是杆秤。”直到如今,村里乡亲都感念这个好人,每听说她回到老家,都上门看望她,彼此说不完的知心话。
不义之财别取,一定干好工作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1969年,韩爱臣22岁时,与当地优秀青年许谦迎结为伉俪,在大张楼镇许楼村,开启了新的人生。
那个时候,这对年轻夫妇最怕的是过年。他们分家另过的当年,过年的几斤白面,还是靠着亲戚接济的。但生活不负有心人,时光衍生着美好的希望。
1975年,在二儿子周岁生日那天,丈夫正式成为山东农业大学的学生。爸爸上大学,妈妈忙农活,小哥哥照顾小弟弟。但哥俩再是听话,毕竟年纪小,常难以自顾。弟弟曾历经大难,险些致命。
1976年冬天,弟弟在院里玩耍的时候,跌入注满水的污水坑,等大人发现时,已被脏水呛昏迷了。家人心急如焚地将他送往公社医院,打了三袋子氧气,住了十多天院,才算保住一条小命。
家里人劝韩爱臣,“赶紧通知孩子爸爸,快让他回来看看孩子。”韩爱臣说:“他学习任务重,怎么能让他分心?”“是学习要紧,还是孩子的命要紧?”“不能这样比。都要紧。他不来,咱全力救孩子。他来了,也得听医生的。我是孩子亲娘,有啥不放心的。”
还有一次,大儿子放学回家,路过邻居家门口,不小心被驴踢伤了嘴巴,孩子本来疼痛难忍,邻居却说:“咋不踢别人,专踢你?”韩爱臣听了这话,也想说个理儿,但为了邻里和睦,吞下泪水一笑了之。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韩爱臣最欣赏的话就是“悲时不言,喜时不诺,怒时不争”“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这是她信守的做人原则。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韩爱臣眼里流下的泪水,和身上流下的汗水差不多。家里再苦再难,她从来不与丈夫诉说,只报喜不报忧。韩爱臣知道,丈夫读大学,其实并不轻松。他1965年初中毕业,1975年去上大学。十年间,当着村里管区里干部,却一直在家乡务农。眼下,猛地进了大学校园,负担也不小。三年大学,丈夫几乎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也很少回家,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学习。偶尔回老家一次,小儿子哪里还能认出他这个爸爸?小嘴凑到妈妈耳旁悄声地问:“这个人,是谁啊?”妈妈听了,笑着却含泪告诉他,“是你爸爸呀,你不想爸爸吗?快叫爸爸啊。”
做丈夫的看在眼里,至今也疼在心里。他私下里对记者说:“老韩这个人,为人要面子,自尊心强。家庭中的困难,再大再重,都是自己硬扛。即使挨三天饿,别人问她吃饭了吗,她也会说吃过了。”“她作为一个女性,看似柔弱,却有一颗坚强的心,从来都是淡化苦难,笑对人生。”知妻若此,也堪为知音了。
丈夫在大学表现突出,担任山东农业大学学生会主席,兼任班里党支部书记,毕业后留校工作。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余松烈教授指导下,他积极配合徐阿炳教授等科研人员,选育出了“山农辐63”高产小麦,荣获国家科技成果发明奖。在山东农业大学,丈夫做学生三年,当老师四年,七年后回到嘉祥,在科委、农业局、农村工作部和县委工作过,1990年到市计生委工作,1997年到原市中区委工作,后被组织提拔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韩爱臣友善待人,家里家外,关系融洽。她说,只有对别人好,别人才能对你好;一定要与人为善,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她常用自己的钱,为婆家的嫂子、弟妹买衣服或好吃的,亲手送到她们家中。嫂子、弟妹也想着她,把老家种的青菜给她送来。在许家这个大家庭中,不论侄子分家还是调处纠纷,只要她一出面,就能息事宁人,因为她处事公道正派。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啥大人啥孩子,啥萝卜啥苔子,己正才能正人。”韩爱臣说。农活再忙,生活再难,韩爱臣对孩子的教育从不放松。好在两个孩子都很乖,从来没挨过训斥,更没挨过打。老二性格好动,特别喜欢摸鱼,见水就想去玩,老大就要管他,兄弟俩就闹意见。每当此时,韩爱臣总是温言相劝,说得兄弟俩心服口服。
韩爱臣教育大儿子,给爸爸写信,让爸爸在大学好好学习,不要挂念家里。儿子在家要好好读书,长大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对国家有用的人。孩子晚上做作业,妈妈都是等孩子做完再去睡觉,从来不看电视。
从1990年到1997年,韩爱臣的丈夫担任市计生委主任八个年头。有些人为自己的事找到门上,送钱送物,韩爱臣一概拒收,但在当时,又岂能是一个“拒”字了得,有的时候甚至难为得掉泪。有人扔下“东西”就跑,她只好去邮局,给人家一一寄回。
当面教子,背后相夫。老韩常对家人说,不义之财别取,要干好工作,对得起国家。丈夫或孩子下班拿回家的东西,不论多与少,她都要问清来由。正是她的叮嘱提醒,丈夫和两个儿子都积极上进,努力工作。
韩爱臣常对儿媳和侄媳说:“咱们女人在家不光学会做家务,还要学会友善待人,相夫教子。”还常交待她们,“好孩子不是打出来的,是哄出来的,是教育出来的”“好媳妇不是骂出来的,是夸出来的,引导出来的”“育儿育孙,用情用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形也正心,正人先正己”。
韩爱臣用自己编的儿歌教育儿子,“小笤帚,值万金,扫天扫地扫人心;四面八方都扫到,扫完自己扫他人”。告诫孩儿们,“坑国家,害民家,毁自家,这样的事,亲爹找你,也不能干!”“您爷三个,不论谁出事,我都不活了。”
母爱是人世间最为神奇的力量,爱的陪伴与呵护下,当年的小哥哥42岁成为副厅级干部,弟弟44岁成为县级干部。
丈夫工作劳累,中午需要休息,韩爱臣都是看着表对着点,再提前喊醒按时去上班。丈夫工作出色,两次被授予省劳动模范。几十年来,她每天起来都给丈夫倒一杯温开水,削一个苹果,常提醒丈夫锻炼身体。她从来不自作主张家里开销,不让丈夫干任何家务。说起老伴儿韩爱臣,丈夫满是感激,“她这几十年里,一直支持着我,从没因为家里的事晚过上班时间,总是超前提醒我,脑子里好像安了一个准星。”韩爱臣对孩子们说:“你爸爸身体健康,才是我们家的幸福。”
1984年,韩爱臣的丈夫担任嘉祥县委副书记,她从来不打他的旗号办私事。丈夫担任市中区委书记的时候,司机小吴有一天开车办事,恰巧遇见韩爱臣,就招呼:“韩姨,上车跟一段路吧。”她说什么也不上车,“老许坐的车,是公车,干工作用,我不能坐,不能跟着沾光。”
1986年,丈夫借调到山东省委办公厅工作,八十多岁的公公突然去世。当时家中哥哥、弟弟和街坊劝她,打电话让老许回来为老人发丧,她都没答应。她说:“三天前他刚看望了老爹,该尽的孝已经尽了。他是县委副书记,目前又在省委办公厅工作,如果他回来,不该来吊唁的也会来,人来多了对他影响不好,甚至还有人可能写信告状,我要对他负责。”韩爱臣代行孝子之礼,老人入土为安。
人只要有志气,就定能干成事
韩爱臣的丈夫上大学去了外地,工分自然挣得更少,生活更得精打细算。1976年的中秋节,别人家买来了鱼肉准备过节,韩爱臣娘仨一共花了一毛五分钱:五分钱的葱,一毛钱的萝卜,喝咸汤,吃烙饼,就过了节。她对孩子说:“咱们节省一点是一点,谁有不如自己有,你爸爸上大学用钱。”后来她风趣的对丈夫说:“人家过节,俺也过节,这不也过来啦,没隔在节那边。”
韩爱臣是重仪表的人,却不奢侈,一直买反季节差价衣服。腰带用断了,就用绳子缝补接上。次子要穿长子穿小的衣服,不轻易买新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她教子孙养成节俭习惯,因为她懂得“俭以养德”的道理。
过惯了节俭日子的韩爱臣,至今买东西还是挑减价的。全家的饭,一般都是她来做。她有一句“名言”,在全家“流行”:“饭店里的饭再便宜,也没食堂的便宜;食堂的饭再便宜,也没自己做的便宜。”而在家里吃饭,也不许浪费,饭菜要吃干净,而且她带头捡孬的吃,好吃的让给儿孙们。她成了全家的榜样,儿孙们学会勤俭了,丈夫吃饭也主动挑孬的吃。
韩爱臣常对丈夫说,人只要有志气,没有干不成的事。在丈夫上大学的第三年,她参加了嘉祥县妇幼保健站举办的培训班。离家15公里的三个月,同学强拉硬拽,她才跟着去看过一场电影,看完又后悔耽误了时间。考过的卷子、做过的试题,她反复地抄、反复地做,有的要做三四遍,无形之中,比别人多学了好多。培训班结业时,她的成绩是全班第二名。一箱子书和笔记,一本结业证书,一本奖励证书,是对她刻苦学习的馈赠。
再长的旅途,也有驿站;再宽的河流,也有码头。2008年,韩爱臣在济宁市人寿保险公司光荣退休。一些老同事说起这位老大姐,敬爱的话语里,满是褒奖。她负责单证库管理工作,把原来千头万绪的仓库收拾得井井有条,发放的单证无一差错。她说:“对于手头的工作,只能提前做好,不能疲于应付。”
那时的韩爱臣一边工作,一边还要料理家务,照顾孙子孙女。两个孙儿上幼儿园和小学,大都是她接送。丈夫心疼地说:“四十多年来,老韩都是早晨六点前起床,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都是她干,在我家是最辛苦的人。她的辛苦,给全家带来了和睦幸福。”
儿孙绕膝乐享天伦,生逢盛世安度晚年
“拿起铁锤是工人,拿起锄头是农民;拿起枪杆是士兵,拿起笔杆是诗人”——这是六十多年前,韩爱臣的二年级语文课文,她至今倒背如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她说这些幼时的梦想,现在全都成真,甚至超越梦想。她常对家人说:“现在吃不愁,穿不愁,住着楼,看病国家付钱,退休了还涨工资,没想到晚年这么幸福,从没见过这样的社会,哪个国家也比不上中国。”
韩爱臣退休以后,家人和朋友都提出请她出去转悠着玩玩,她都推了。有一次,儿子给她买好机票,想让母亲去法国旅游,她说什么也不肯,终于还是退了机票。对她来说,心安之处便是美景。中国最好,家乡最好,家里最好。
韩爱臣对老伴说,咱俩还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教育儿孙做好人,行好事,为国为民多做贡献;一个是锻炼好身体,健康养生,活大年纪,享受社会,安度晚年。
如今的韩爱臣,神清气爽,脑聪目明,每天走一万步以上,天天做老年操,还上网玩游戏。她经常用毛主席的话教育儿孙,“‘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希望你们一辈子做好事。”她用柔软慈悲的心,爱着幸福的一家人,对孙子辈的要求也更严格,时常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教导教育他们。
孙子从一岁到高中毕业,孙女从一岁到上初中,都是韩爱臣带,吃住、接送几乎全包,妈妈喊他们回家都不回,就愿意跟着奶奶。晚上娘仨打地铺睡在一起,老韩躺下把两个胳膊一伸,这边枕着孙子,那边枕着孙女。在祖母的慈爱之下,两个孙儿都考上了中外名校。孙女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考入中科院工作;孙子今年山东大学毕业,考上了国外名牌大学研究生。
儿孙们周末来家吃饭团聚,儿媳想帮忙做个菜、洗个碗,韩爱臣都不肯让她们动手,“你们平时工作太忙,忙得和孩子见面都难,见了面亲都亲不够,就陪着孩子说说话吧,这点活累不着我。”
韩爱臣精气神再好,毕竟年逾古稀。孩子们怕她过于辛苦,几次提出来给家里找个保姆,可无论怎么做工作,她始终不同意。她的理由是,“你们找来保姆,别人给咱家干活,我看不下去啊。除非让保姆闲着,还是我来干活做家务。”就这样,找保姆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啦。
平日里,儿子儿媳偶尔拌个嘴,她都先批评儿子,弄清了原由再说情理,孩子们心服口服。儿子夸奖说:“妈妈学历不高水平高。”儿媳对别人说:“在俺这个家里,谁要不孝敬妈妈,天理难容。”婆婆退休前,每当发了奖金就问儿媳,“妈妈发奖金了,你们需要什么,我给你们买去。”儿媳进门的时候是本科学历,在婆婆的支持下,现在是研究生了。媳妇夸婆婆说:“比亲娘对自己都好。”
说起自己的老伴,丈夫总是满怀感激之情,“我的姥爷姥娘、父亲母亲、儿子媳妇、孙子孙女,加上本人,上下五代,老韩都服务过。”他说得十分真诚,话语里充满敬爱。
韩爱臣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单位,与人为善、辛勤奉献,敬老爱幼、修身齐家……这就是她至高至纯的人生哲学,也是她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实践。
75岁的韩爱臣,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她用美好的心灵和勤劳的双手,给很多人带来了幸福,也理应收获和分享这幸福。
■苗青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