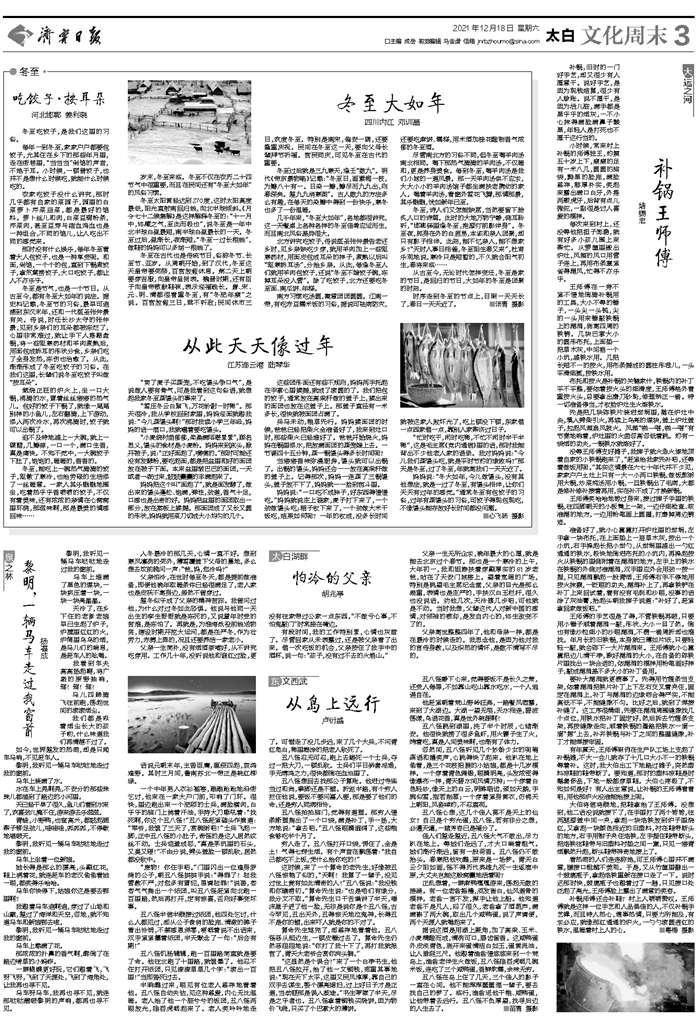补锅,旧时的一门好手艺,却又很少有人愿意干。说好手艺,是因为现钱结算,很少有人赊账。说不愿干,是因为活儿脏,满手都是黑乎乎的烟灰,一不小心抹得满脸满鼻子黢黑,年轻人是打死也不愿干这行当的。
小时候,常来村上补锅的师傅姓王,约摸五十岁上下,瘦瘦的足有一米八几,圆圆的脑袋,黝黑的脸庞,满脸慈祥,憨厚朴实,笑起来露出满口白牙,外搭两颗虎牙,后背有点儿微驼,一副很是讨人喜爱的模样。
每次来到村上,还没等他把担子卸稳,就有好多小孩儿围上来帮忙。从箩筐里搬出炉灶,风箱的风口用管子连上,再用布条塞紧省得漏风,忙得不亦乐乎。
王师傅在一旁不紧不慢地倒腾补锅用的工具,大小不等的锤子,一头尖一头钝,尖的一头用来锤敲铁锅上的漏洞,剥离四周的铁锈。几块巴掌大小的圆形布托,上面垫一把草木灰,中间掐一个小坑,盛铁水用。几把长短不一的按火,用布条搓成的圆柱形卷儿,一头平滑细腻,按铁水用。
布托和按火是补锅的关键家什,铁锅内的补丁平不平整,要依着按火头的细滑度,王师傅格外看重按火头,总要拿出磨刀砂轮,修理矫正一番。待一切准备停当,才收拾炉灶生火炼铁水。
先是把几块碎铁片装进坩埚里,搁在炉灶中央,填入劈柴引火,再续上乌亮的煤块,盖上炉灶盖子,拉起风箱扇风拔火。风箱“啪—嗒,啪—嗒”有节奏地响着,炉灶里的火苗忽高忽低着跳。约有一袋烟的功夫,一锅铁水就炼好了。
没等王师傅支好摊子,我婶子就火急火燎地顶着自家的小铁锅跑来了,“赶紧给我家先补吧,还等着做饭用呢。”其实这情景在六七十年代并不少见,家家户户土灶上只有一大一小两口铁锅,做饭熬粥用大锅,炒菜炖汤用小锅,一旦铁锅出了毛病,大都是修补修补接着再用,实在补不成了才换新锅。
王师傅笑哈哈地转过身来,接过婶子手里的铁锅,往四脚朝天的小板凳上一架,一边仔细检查、核准漏的地方,一边用粉笔画上圆圈,打磨掉周边锈迹。
准备好了,就小心翼翼打开炉灶里的坩埚,左手拿一块布托,在上面垫上一层草木灰,按出一个小坑,右手操起长把小坩勺,从坩埚里盛出一勺红通通的铁水,极快地倒进布托的小坑内,再操起按火从铁锅的里侧附着在漏洞的地方,左手上的铁水在铁锅的外侧对准漏洞,双手里应外合用劲一按一捏,只见漏洞飘起一股青烟,王师傅右手不停地用按火抹擦,一眨眼的功夫,漏洞补上了,再拿铁铲在补丁上来回试着,看有没有毛刺和沙眼,没事的话涂了灰油膏,抬起头朝我婶子说道:“补好了,赶紧拿回家做饭吧。”
王师傅的手艺很是了得,不管铁锅再破,只要用小锤子顺着漏洞一敲,形状、大小一目了然。倒也有像沙粒细小的沙眼漏洞,不费一番周折却也难找。年月长的旧铁锅,本身就已薄如片纸,只要轻轻一敲,就会碎下一大片漏洞来。王师傅就小心翼翼把边儿清干净,瞅好漏洞的大小,在自备的碎铁片里找出一块合适的,依漏洞的模样用粉笔画好样子,敲成漏洞差不多大小的补丁备用。
要补大漏洞就更费事了。先得用竹篾条当支架,依着漏洞把铁片补丁上下左右交叉着夹住,固定在漏洞上,补丁与漏洞的边缘吻合得严实,不能高低不平,不能缝隙不匀。比好之后,就到了焊接补缝了。这工序很精细,先要在漏洞周围缝隙找几个点位,用铁水把补丁固定好,然后拆去竹篾条支架,再按缝隙走向,顺着铁锅的璺路把铁水一滴一滴“摁”上去,补齐铁锅与补丁之间的整圈缝隙,补丁才能焊接牢固。
有年夏天,王师傅照例在生产队工场上支起了补锅摊,不大一会儿就存了十几口大小不一的铁锅等着补。这时,我大伯出工下地路过摊子,突然塑料凉鞋的鞋带断了。要知道,那时的塑料凉鞋是时髦奢侈品,下地一般都穿草鞋。大伯心疼极了,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出主意说,让补锅的王师傅看看吧,用他那炉火没准能给接上呢。
大伯将信将疑地,把鞋拿给了王师傅。没想到,他二话没说就接下了,在手里打了两个转转,往两腿膝盖中间一夹,拿起一块烙铁放到炉子里烧红,又拿起一块颜色相近的旧塑料,衬在鞋带断头的地方,右手用钳子夹住烙铁,左手捏住鞋带断头,把烙铁往鞋带与旧塑料衬垫之间一塞,只见一缕青烟飘然升起,断头鞋带神奇地接上了。
看热闹的人们连连称绝,可王师傅心里并不满意,嫌接口粗糙不美观。于是,又从竹筐里翻出一个玻璃瓶子,拿起烙铁重新在接口走了一下。说时迟那时快,玻璃瓶子也跟着过了一趟,只见接口处泛起了亮光,王师傅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补锅师傅还会补鞋?村上人啧啧赞叹。王师傅就是这样一位手艺和人品俱佳的人,不仅补锅手艺棒,而且待人热心,遇事热情,只要力所能及,有求必应,就像那红通通的炉火,一勺勺滚圆透红的铁水,温暖着村上人的心。■粤梅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