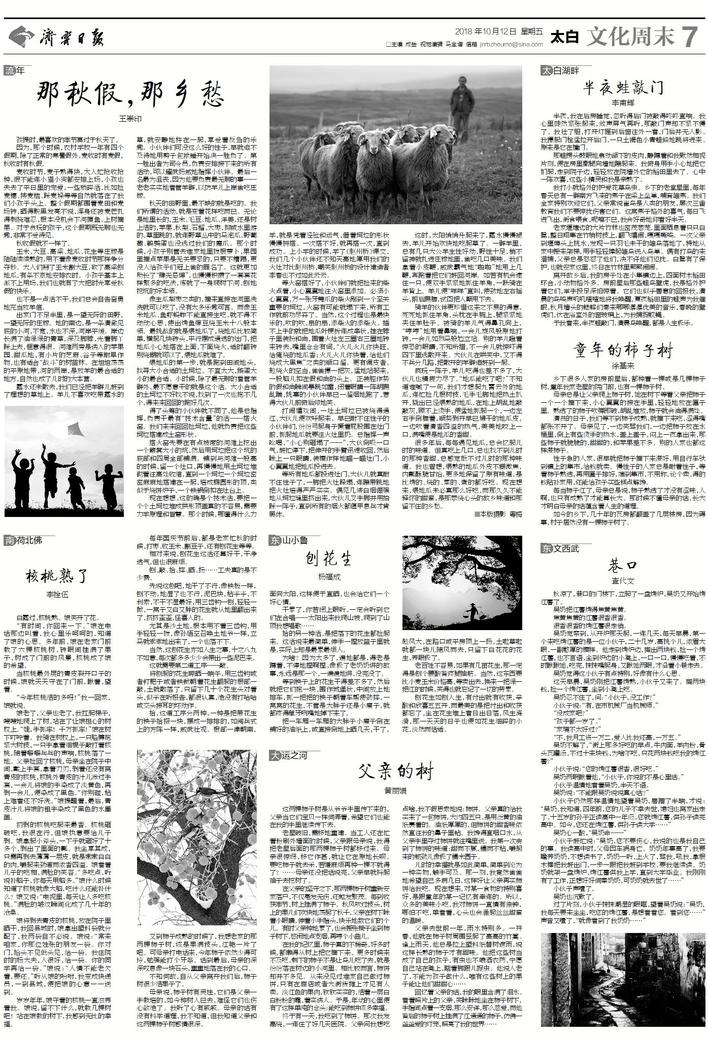又到柿子成熟的时候了,我想老家的那两棵柿子树,该是果满枝头,红艳一片了吧。可母亲打电话来,今年柿子依然少得可怜,勉强能打个牙祭。话到最后,母亲的深深叹息像一块石头,重重地落在我的心口。
不知何故,自从父亲离开我们后,柿子树很少结果子了。
母亲说,柿子树有灵性,它们是父亲一手栽培的,如今种树人已去,难怪它们也伤心欲绝了。我听了心有戚戚。母亲的话有没有科学道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父亲和这两棵柿子树感情很深。
这两棵柿子树是从爷爷手里传下来的,父亲当它们宝贝一样伺弄着,希望它们也能在我的手里继续传下去。
老屋破旧,需移地重建。当工人还在忙着粉刷外墙面的时候,父亲跟母亲说,我得把老屋后面的那两棵柿子树都移过来。母亲很惊讶,移它作甚,就让它在原地长呗。要吃柿子就去采,若嫌麻烦再种一棵不就得了?……母亲还没把话说完,父亲早就捋起袖子去挖树了。
在父亲的坚守之下,那两棵柿子树重新安家落户,不仅毫发无伤,还越发繁茂。每到收获季节,树上挂满了柿子。秋风吹过枝头,树上的果儿们欢快地荡起了秋千,父亲在树下眯着小眼睛,伸着小手指头,快乐地数它们的个儿。有时父亲种地累了,也会搬张椅子坐到柿子树下,悠闲地点支烟,再哼个小曲儿。
在我的记忆里,柿子真的不稀奇,好多时候,都懒得从树上把它摘下来。更多时候来不及吃,剩下的柿子不是让鸟儿吃了去,就是纷纷落在树边的小河里。相比较而言,柿饼却并不多见。从来没见过谁家自己做过柿饼,只有在商店或者大街货摊上才见有人卖。淡红色的果肉,软软实实的,结着一层白白粉粉的霜,着实诱人。于是,年幼的心里便有了这样单纯的念头:能吃到柿饼该多幸福。
终于有一天,我吃到了柿饼。那次我发高烧,一连住了好几天医院。父亲问我想吃点啥,我不假思索地说:柿饼。父亲真的给我买来了一包柿饼,大约四五只,是用泛黄的油纸裹着的。油纸厚厚的,但柿饼的甜香味依然直往我的鼻子里钻。我馋得直咽口水,从父亲手里夺过柿饼就往嘴里送。我第一次尝到了柿饼的味道:甜而不腻,糯而不粘,嚼起来的韧劲儿像极了糯米圆子。
儿时的幸福就是如此简单,简单到沦为一种实物,触手可及。那一刻,我竟然偷偷地希望自己多病几日,这样好让父亲再买柿饼给我吃。现在想来,对某一食物的特别喜好,是跟童年的某一记忆有牵连的。所以,众多的美味小吃,我对柿饼一直情有独钟,哪怕不吃,单看着,心头也会涌起丝丝甜蜜的温暖。
父亲去世前一年,雨水特别多。一开春,他就在柿子树周围竖起了高高的竹篙。逢上雨天,他总是拉上塑料纸替树遮雨,说这样长熟的柿子才有甜味。他把这些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有虫也不喷洒农药,宁愿自己站在凳上,踮着脚跟儿捉虫。他说人老了,不能为孩子做什么,唯有这些树上的果子能让他们甜甜心……
回忆着父亲的话,我的眼里含满了泪水。看着照片上的父亲,笑眯眯地坐在柿子树下,手指间点着一支烟,那么安详,那么慈爱,而他背后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红通通的柿子,仿佛一盏盏爱的灯笼,照亮了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