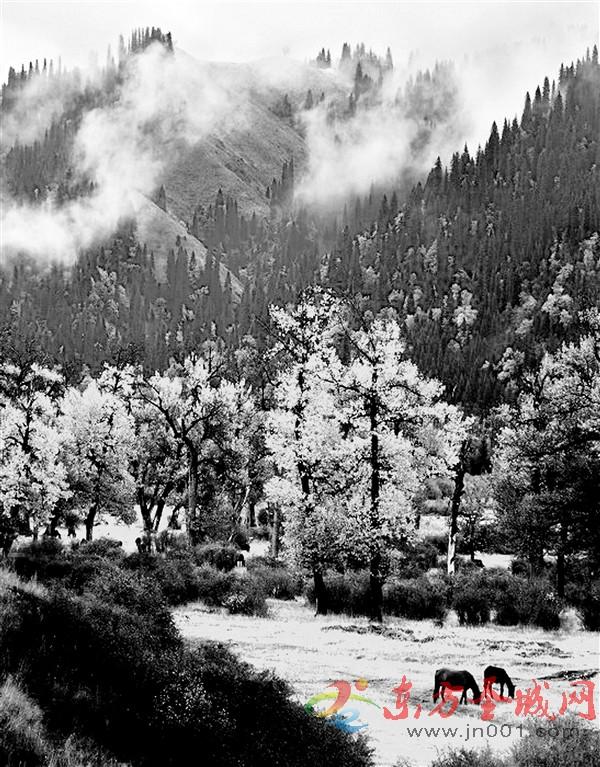
唐诗里的秋天 付振双 久在城市,名曰生活,却像极了几点间的转悠,忙着来,急着走,少不了“匆匆”二字。城里的秋,总是“匆匆”,于来去中,叫人觉着没有面孔,难以辨认。木叶落,草虫鸣,鸡犬相闻,那是故乡的秋,多迷人,但它们离我太远。于是,喜欢上了唐诗。 在那里,秋天像父母,任时光老去,仍固守着我离开时的模样。唐诗里的秋天,那么近人,好比晚间遇到的那位老人。他在安静的小河边上边走边唱,旁若无人,却情如秋水,微微荡漾,直荡得人身晃晃,心悠悠。唐诗与秋天,或是最佳组合,最美传奇。如此黑夜,唐诗里的秋歌,怎会少! 最想读的还是王维和孟浩然。“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是王维的歌。那时,好山好雨好天气,明月清泉石头,怎么读着,都是美的享受,静心的节奏。甚至,一幅大自然的画卷随着字符始而描绘,随着音韵停而结束,上面还写了个大大的“禅”字。难怪王维号摩诘居士,人称“诗佛”,诗句如画似偈。至于某些诗章,一两句便可化掉人心,如“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女主人公想念丈夫之态,竟催人泪下。 夜里,母亲打来电话,问我,吃煮花生吗?我说,想。母亲说,有空回来吧,花生嫩不久。我闪烁其词。母亲笑着说,也就是问问,没想你回来,想吃捎给你。临了,母亲还说,不用你惦念,我们很好。 “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凉。炎炎暑退茅斋静,阶下丛莎有露光”。一千多年前,孟浩然在他的歌中感知着初秋的快意,自然的灵动变化,还流动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满足。没曾想,长大成家后,自己颠沛流离,母亲也已流离失所,我的秋夜啊,与母亲的秋夜,可一样凉? 这么多年来,一路走过,仍记得儿时学孟浩然的诗,“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老师读一句,我们读一句。那时的我们,想得东西少,一动就是笔杆子,可记住的东西不在脑子里,是在骨子里。如今,读王维、孟浩然,还有众多诗人的诗,只看到篇目,想起的还是多年前课堂上的画面。 流光易把人抛,多年一晃就过,年幼的长大了,长大了的年老着,年老的失去着。故乡的土地,长着秋的根,长着人的魂,连着不息的情愫。“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且随着孟浩然的足迹,上路,“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但愿一切不是梦。 我的心尖一颤,唐诗里的秋天,也是秋天的唐诗,诗的巅峰,同样有自然之美,有人情之暖,也有生活之适。唐诗里的秋天,分明是一部秋的《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