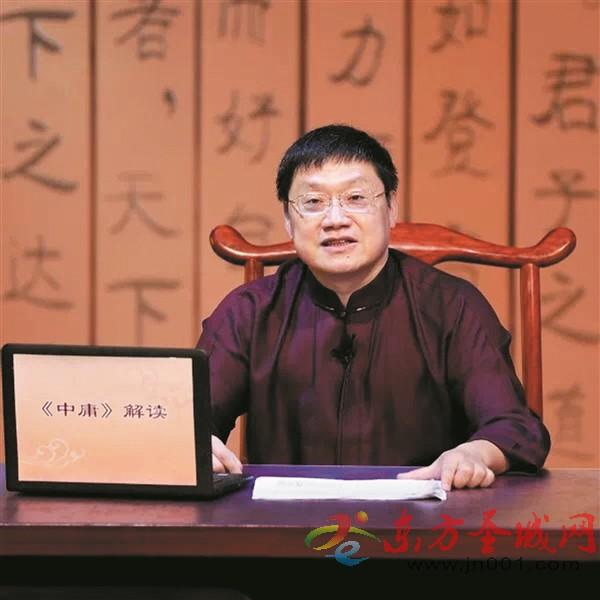7月12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肖永明,带来《中庸》解读第十讲——《至圣之境》。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渊博的视野,对“至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与诠释,对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儒家“为下不倍”之义、“居上不骄”之说,以及孔子传承道统之功,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当中的第三十一篇。《中庸》和《大学》一样,都是从《小戴礼记》里面抽出来的,像《大学》就是其中的第四十二篇。
《中庸》原先在汉魏时期并没有学者特别关注,直到唐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韩愈,以及他的弟子李翱,开始强调《中庸》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创立儒家心性之学,以对抗佛道之学的非常重要的思想依据和重要的文本依据。
到宋代以后,不管是当时的统治者,还是学者,都对《大学》《中庸》特别的推崇。这些著名学者所进行的经筵讲学过程当中,《中庸》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一些大儒,都担负着去给皇帝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学》《论语》《孟子》《易经》等等儒家的核心经典,都是重要的内容。《中庸》,在当时也处于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
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占有很重要地位的是宋明理学,最早兴起在北宋。理学家对《中庸》特别重视,在他们看起来,《中庸》记载了儒家的圣圣相传之道。用朱熹的说法,就叫做孔门传授心法。像北宋的时候,范仲淹、胡瑗、欧阳修,这些著名的儒家学者,都对《中庸》有比较深的研究,都留下了相关的著作或者论断。尤其是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灏、程颐,他们从理学的角度去对《中庸》当中的内涵进行了阐发,对《中庸》的思想进行了创新性的发挥。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南宋。作为宋明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最终把《中庸》从《礼记》当中比较彻底的抽离出来,就做了一个《中庸章句》和《中庸或问》,对《中庸》进行了非常深入和细致的阐述。他把《中庸》《大学》和《论语》《孟子》这几个书一起合编就成为四书,写成了一部作为朱熹代表作的《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有非常高的地位。宋代以后,特别是元代中期以后,直到二十世纪初,这部书在科举考试当中,在学校教育、书院教育,各种各级官学教育当中,都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读本。
《中庸》27章原文: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是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大哉是一个赞叹之辞,赞美之辞,在《周易》的乾卦,以及在《论语》里面孔子对尧的称赞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用法。《周易》乾卦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首先是赞叹赞美,然后孔子在赞叹尧的时候,大哉尧之为君!这里就是对圣人之道的一种赞美。在这个赞美之后,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这个圣人之道值得赞美,为什么它这么伟大。
第一个角度,“洋洋乎”就是充满流动,是说圣人之道是流动的。峻就是高大,峻极于天是说天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圣人之道,它的高大是和天一样的。至大无外,就是没有比圣人之道更大的了,就像天一样的,把所有的东西都覆盖了。
第二个角度,就是“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刚才第一句是说圣人之道,从大处来说是在天地万物当中皆见其大。这一句事实上就另外一个层面,从小的层面说,贯穿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细节当中,一些礼仪规范当中。从圣人之道和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当中。
中国古代就是一个特别强调礼的社会,我们的古代文明是礼乐文明。在古人的观念里面,礼是源于天道的。礼是一些具体的规范、规则、原则,好像是人为去制订的这么一些规则。但是在古人的观念里面,礼是有它的天道依据的,是天道的一个体现,不是我们人为的。这在《尚书·皋陶谟》里有一句话,“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
“天工人其代之”,就是人间的君主代天来理政,代老天来治理统治人间社会,治理天下。那么人间的君王,他的职责就是代天行政。天秩有礼,这个说法,事实上就是说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礼仪规范,它同样是天道的一种体现,是来源于天的。
《中庸》作为《礼记》当中一篇,是要解释礼的。对礼的一个基本的认识观念就是,有天道依据。那么在这句话当中,“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具体是什么含义呢?朱熹对它有一个解释,他说礼仪三百是指我们看到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这一些比较大的礼仪。威仪三千,就是指一些更加细致的礼仪的规定。比如日常生活中,对服饰的一些要求,对言行的一些要求,怎么坐,怎么立,怎么行等等,这些言行的一些规定,那就非常细致的有三千之多。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头,礼的功能确实是非常强大的,经常会谈到的就是“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一个人基本的行为规范,立身处世的一些基本的规范原则。孟子也说到,礼门义路,礼是我们进入社会的一个门径,一个基本的途径。那么,礼的社会功能,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对我们日常生活基本运行规则的规定。所以在古代社会里头,礼就是一个社会所运转的基本的逻辑。人的生活,整个的社会秩序的维持,都离不开礼。
这里说到的礼仪三百也好,威仪三千也好。不管是礼仪,还是细致的礼仪的规定,都是强调礼仪规范。从大的方面来说,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需要礼;小的来说,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需要按照礼的规定来进行。所以,三百、三千,虽然看上去大大小小很多,但这其中蕴含的这就是道。不管是礼仪三百,这些大的礼仪也好,还是日常生活种种细节也好,它都体现了道。
这些礼仪等待圣人出现以后才能实行,假如没有至高的德性,要把伟大的事业做成功,那是不可能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几句话在《中庸》中非常重要。
“尊德性”,开发自己内在的光辉的德性,这是对内。对外要好好地去“道问学”,要努力请教、学习、探讨,把自己的内德和外学结合起来。“致广大而尽精微”,追求广大——上天入地,对整个宇宙天地万物了然于心。但是,对极其微观的世界、极其微小的事理,也要“尽精微”,用心思去穷尽它。“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接物、待人、处事方面,要达到极其高明,就是思维、思辨、明辨极其高精澄明。但做人在言谈举止和行为措施上,要实行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文质彬彬。只有温习过去的那些经验教训,才能够知道自己未来怎么做。把自己修养成拥有敦厚的德性,才能尊崇礼仪。这样才能从内到外,从上到下,都显示出一个君子的光辉形象。
国有道和国无道时,君子的选择问题。“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作为领导,不能骄奢淫逸;作为下级,不能背弃背叛。“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这句话非常重要。儒家传统不是愚忠,不是说国有道也忠,国无道也忠,明君也忠,昏君也忠,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和精神操守。相反,儒家强调国家清明和谐、万物兴旺、百废待兴时,君子应去发表言论,施政自己的纲领,使国家振兴起来。当国家昏暗无道时,应以他的沉默对抗表示绝不跟随,以他的沉默表现出自我的特立独行。因为知识分子是作为文化载体、文化传承者和思想者而存在的,当政治清明时,他们的言论足以兴邦,使国家兴盛富强。但是,当政治黑暗时,他们全身远祸,以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启迪感召后人。
所以,《中庸》是儒家的传道之书。在读《中庸》的时候,确实要去思考儒家的精神内核。儒家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究竟是什么,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去传承?在我们特别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时,怎样去理解、体会《中庸》,把这些经典的文本真正的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言行思考当中,这样,对于我们理解儒家文化的内涵,自觉的去担负文化传承责任,在这些方面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