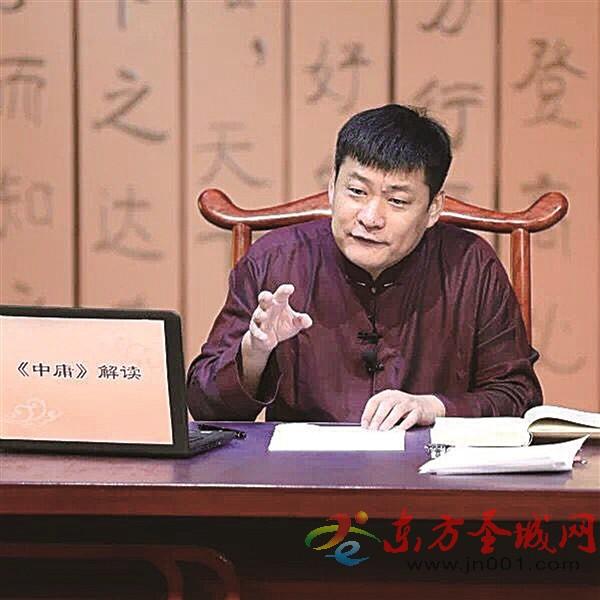6月26日,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孔德立带来《中庸》解读第八讲——《诚明之道》。讲座中,孔德立对《中庸》“诚”的思想做了细致解读,透过旁征博引,重点论述了达成诚明之道的工夫修养。孔德立指出,“诚”为真实无妄之义,由“不诚”达至“诚”,是一个“择善而固执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属于“择善”,“笃行”则是“固执”。作为道德修养主体的人,只有接触客观知识,进而认识明辨之,并将这一切坚持笃行下去,才能从容中道,达至诚明境界。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中国人对诚这个概念是情有独钟的。我们常说一个人实诚不实诚,用实诚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这是《中庸》本身的一个概念。诚的概念就是实,实在,不虚不假。诚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又显得弥足珍贵,因为现在很多不诚的现象出现了。
诚,真实无妄的意思。天指自然,天之道就是自然之道,或自然的规律。自然界的一切,宇宙万物都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没有虚假。真实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础,虚假就没有一切。所以说,诚是天之道。人之道,是指做人的道理或法则。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道与天道一致,人道本于天道。《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都反映了这种思维方式。讲到诚也是这样,既然诚是天之道,人之道就应该思诚,思诚就是追求诚。思诚者,人之道,就是说追求诚是做人的根本要求。这段话是从宇宙万物存在的现实和规律上,说明了诚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础,因此也是为人的根本,这就从根本上论证了诚的意义。
事物本来的状态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诚是没有经过粉饰,没有经过人文加工的这么一个真实的存在。既是自然界的一种真实的存在,又是人的思想的一种真实的存在,所以这听起来有点像老子讲的自然之道。实际上,儒家讲的诚,确如道家讲的道的意味,非常相似。
潜藏的这一核心理念早已被朱熹所点破,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章句》注解《中庸》时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依朱熹之见,中庸精神或者说是中庸之道是建立在“真实无妄”的天道之“诚”的基础之上的。那么,“真实无妄”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尊重客观事实。钱穆先生在其《朱子学提纲》中也说道:朱子认为:“诚只是实;诚是理;诚是实有此理;诚在道为实有之理,在人为实然之心;不观中庸,亦有言实理为诚处,亦有言诚悫为诚处。诚就是真实无妄,就是天理之本然,反之,天理之本然亦是宇宙本体之诚的体现”。而作为体现诚之本体的宇宙之道,不是凭空而来,乃是基于圣人君子“格物”“致知”的思维成果。圣人君子通过“格物”“致知”获得的知识和思想,这些知识和思想即是对宇宙万物的规律,以及圣人君子对自我的认识规律的把握而形成。然而,更重要的是代表宇宙万物的规律以及圣人君子自身认识规律的所谓“道”,都是圣人君子不可背离的与不可违逆的,正如《中庸》所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真实的宇宙,诚信的自然,即是圣人君子不可背弃的“道”的本体,而这一宇宙万物的本体——“道”,其核心精神即是“真实无妄”的“诚”的显现,同时它又以“真实无妄”的“诚”为归宿。而认识了“道”即是“诚”的本体性与真原性的同一时,才可以确定圣人君子必以“至诚”和“诚明”的正确心态与姿态,来应对万事万物的变化与发展。
所以,中庸精神来自于圣人君子对“道”的“真实无妄”的深切体悟,来自于圣人君子对“ 天理之本然”的真诚信奉和遵循,而不是流于表面形式的“执两用中”,更不是纯粹以平衡矛盾为手段,以妄顾事实为能事的所谓“中庸之术”。因之,如果失去了对宇宙之道“真实无妄”的“诚”的本体精神的体悟,中庸之道必然会被误解为肤浅的明哲保身、八面玲珑,甚至是两面三刀、损人利己的“中庸之术”。因为在孔子和儒家的先贤们看来,不能达于“至诚”和“诚明”的智慧境界,则不能达于“至德”的中庸之境。
“诚”不仅是万物本源,生命之根,更是宇宙的永恒动力,故《中庸》中说,宇宙之道“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王船山《船山思问录·内篇》中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一动一静,阖辟之谓也。由阖而辟,由辟而阖,皆动也。废然之静,则是息矣。‘至诚无息’,况天地乎!”
有动才有“化成”的过程,有了“化成”的过程,才有宇宙万物。所以,动是宇宙之“诚”的表现方式,也是宇宙之“诚”的存在形式,“无息”与永恒运动则是宇宙的“至诚”之性决定的。
“诚”作为存在宇宙的根本动力是无形的,是无声无息的,变化无穷而又不露痕迹。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诗经· 大雅》中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礼记·哀公问》中说:“无为而物成,天之道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张子正蒙·天道篇篇》中说:“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为物不贰也。”在《张子正蒙·天道篇篇》中还说:“已诚而明,故能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船山《思问录》中说:“诚斯几,诚、几斯神。‘诚无为’,言无为之有诚也。”天道无为是宇宙至诚赋予万物自身的神秘力量,这种神秘力量即是“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的注脚和说明,同时,它又把宇宙之“诚”作为圣人君子认识能力之外的一个神秘的真实存在来对待。这说明宇宙之“诚”不是圣人君子能够完全把握的一种伟大力量,圣人君子只有通过自我的努力奋斗,才可以赢得和拥有这种“至诚”精神力量的智慧以及它的支撑,才可以一步一步逐渐地接近“至善”,达到“化成天下”目的。因之,《中庸》中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其实,“至诚如神”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故作高深,它真实反应了万事万物,以及人生、社会、国家政治及其发展的必然规律。
那么人如何才能达到诚的境界呢?孔子的回答是人必须修身、知人、行五道、三德。由此推展开来,提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九种常行大纲及其效用方法。这九项工作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具体而言,要内心虔诚,外表端庄整洁,不符合礼仪的事情不要去做,这就是用来修身的方法;摒弃谗佞小人的坏话,疏远女色,轻视财物,珍视品德,这是劝勉贤人的好方法;尊崇他们的地位,丰厚他们的俸禄,用同一好恶标准以示公正无私,这是劝勉亲人的好方法;给大臣们多设属官,让他们指挥办事,使得他们有精力思考国家大事,这才是抚慰大臣的方法;对待群臣要有忠信,并以厚禄供养他们,这是劝勉士人为国效力的好方法;征役百姓要适时、赋税征收要减轻,这是关怀劝勉百姓努力生产的好方法;每天视察工匠的工作情况,每月考察他们的成就,发放的钱粮工资要与他们的劳动功效相称,这是劝勉工匠努力工作的好方法;对远方的客人要热情迎接,盛情款待,热情相送,对有才能的人要给予奖励,要同情和容纳才能不足的人,这是用来安抚远方藩国和商旅宾客的方法。延续绝嗣的家族,复兴被灭亡的国家,整顿混乱的秩序,支持弱小,让诸侯的朝聘按时进行,薄收他们的贡赋,丰厚天子的赏赐,这是安抚诸侯、使天下畏服的好方法。做好这九项工作,事实上也就处理调节好了九种人际关系。调节这九种人际关系是使天下国家达到太平、合理的重要保证。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到一个“诚”字上,就是要真诚专一。
对于个人而言,修身在于至诚。修身并不是一个人抱经苦读、冥思苦想。首先,从修身的步骤来看,思修身则要事亲,要行孝悌礼仪,要事亲则要求知人,要知人则需知天,天即自然之理。能知天,则知人;能知人,则能事亲;能事亲,则能修身。可见,修身须从明辨善恶始,事无巨细,要做到有节制,随时处中,知行合一,推己及人并将善行发挥到极致。
我们不是圣人,可能有时候比贤人还低,所以我们要直面前行的曲折与困难,甚至是要面临反复。但是只要我们悟得诚明之道,并且不断的努力,就会克服学习中、生活中、事业中的困难。这样我们会不断的克服,不断的成长。虽然我们可能达不到至诚如神的境地,但是我们最起码可成己成物,因为这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础。儒家的文化厚重而悠远,高明而博厚,至诚可与天地参,人立于天地之中,人要与天地功化同流。
中庸之道所真正推崇的,绝不是浮夸浅薄的处世之道,相反,却是更理性、更睿智的哲理——以诚立身,诚化天下,无论在任何年代,这对于社会的发展、人的自我实现而言都具有深刻的启示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