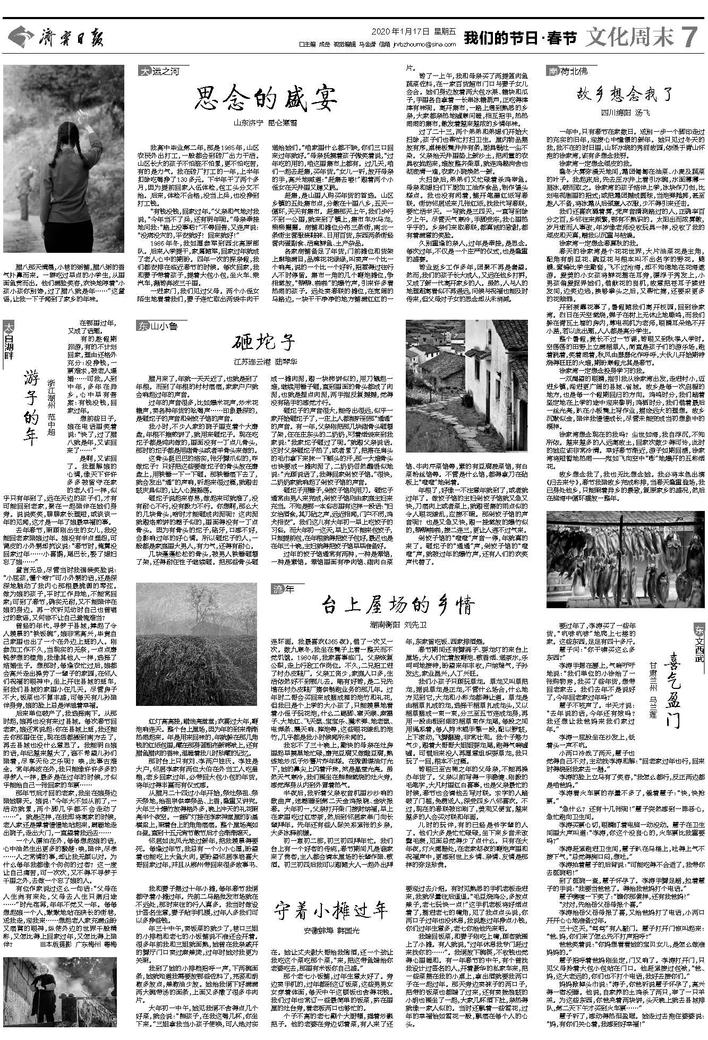红灯高高挂,蜡烛亮堂堂;欢喜过大年,鞭炮响连天。整个台上屋场,因为年的到来渐渐热闹起来。年是用来回味的,年就躲在那几角钱的红纸包里,藏在那身蓝粗布新棉袱上,还有腊鱼腊肉的香味,温暖着我儿时珍藏的记忆。
那时台上只有刘、李两户姓氏。李姓是大户,邻居李家有两位大伯在外当工人吃皇粮,老乡回家过年,必带回大包小包的年货,将年过得丰富而有仪式感。
从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开始,祭灶祭祖、祭天祭地,给祖宗供奉祭品、上香,隆重又讲究。大年三十爆竹放得格外多,晚上冲天的礼花照亮半个夜空。一盏矿灯挂在李家神堂屋的阶基横梁上,照着台上的角角落落。整个屋场亮如白昼,直到十五元宵节散节后才会渐渐熄灭。
邻居如此风光地过新年,把我羡慕得要死。每逢过年节,我总有一个小小心愿,盼望着也能吃上大鱼大肉,更盼望邻居李培喜大哥回家过年,并且从郴州带回来很多故事书、连环画。我最喜欢《365夜》,借了一次又一次。数九寒冬,我坐在凳子上看一整天而不觉饥饿。1980年,我家喜事临门。父亲恢复公职,走上行政工作岗位。不久,二兄招工进了村办皮鞋厂。父亲工资少,家庭人口多,生活依然好不到哪儿去。略有好转,是二兄先增在村办皮鞋厂搞供销跑业务的那几年。过年时二哥会买回来成捆成箱的炮竹和礼花,但我已是个上学的大小孩了,只能羡慕地看着小侄子玩花炮,什么二踢脚、窜天猴、麻雷子、大地红、飞天鼠、宝宝乐、魔术弹、地老鼠、电焊条、震天响、摔炮等,这些眼花缭乱的炮竹,几乎都是我小时候闻所未闻的。
我忘不了三十晚上,勤快的母亲在灶房里起早摸黑地忙碌,磨完豆腐又做酿豆腐,熟练地炒瓜子炒薯片炸年糕。在微弱煤油灯光下,她的鼻尖上闪着汗珠,煞是晶莹光亮。虽然天气寒冷,我们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灶火旁,感觉浑身从内到外冒着热气。
半夜后,我听着父亲收音机里沙沙响的歌曲声,迷糊睡到第二天金鸡报晓、金吠报春。大年初一,父亲打开柴门接财纳福,早上在家里吃过红枣茶,然后到邻居家串门向长辈拜年。先年还有些人际关系紧张的乡亲,大多冰释前嫌。
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年忙。我们台上有一个好客的传统,春节期间凡是谁家来了贵客,主人都会请本屋场的长辈作陪、敬酒。初三初四后我可以跟随大人一起外出拜年,东家留吃饭、西家排酒筵。
春节期间还有舞狮子、耍龙灯的来台上屋场,大人们忙着放鞭炮、敬香烟、递茶水,乐呵呵地接待,盼望来年丰收,户纳瑞气,子孙发达,家业昌兴,人丁兴旺。
我们小孩子只顾玩草龙。草龙又叫草把龙,据说草龙是正龙,不管什么场合,什么地方见到它,大龙和小彩龙都得让道。草龙是由稻草扎成的龙,选择干稻草扎成龙头,又以稻草捆成一束一束,分三至五节连成龙身,再用一段由粗到细的稻草束作龙尾,每段之间用绳系着,每人持木棍手擎一段,配以锣鼓,上下滚动,飞舞翻腾,非常壮观。我个子矮力气少,跟着大哥哥大姐姐耍龙尾,跑得气喘嘘嘘。可惜后来没人再愿意组织耍草龙,我只玩了一回,根本不过瘾。
转眼已至古稀之年的父母亲,不能再操办年货了。父亲以前写得一手稳健、刚毅的毛笔字,大凡村里红白喜事,也是父亲最忙的时候,春节也会请他去写对联。求字的人踏破了门槛,免费送人,深受四乡八邻喜欢。不过,现在的春联被印刷了,美观又便宜,越来越多的人会买对联和年画。
儿时的玩伴,有的已经是爷字辈的人了。他们大多是忙忙碌碌,坐下来乡音未改鬓毛衰,见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只有在大年夜,灯火阑珊处,在老家彻夜的鞭炮声里和祝福声中,更感到世上乡情、亲情、友情是那样的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