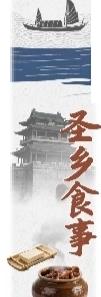■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娜
在济宁,时间是有味道的。
它不单是孔孟之乡典籍里泛黄的墨香,也不仅是运河古道上粼粼波光映照的千年帆影。它更具体,更温热,更熨帖人心——它是一缕缕金黄酥脆、细如发丝的馓子,在滚油中舒展绽放时升腾的烟火气,是咬下去那一声清脆的“咔嚓”,在唇齿间瞬间化开的咸香,以及随之涌上心头的、关于家与年的温存记忆。
这缕在济宁街巷萦绕的馓子香,其实早从千年前的时光里就开始酝酿。
春秋战国时,寒食禁火三日,人们便以“寒具”——一种环钏状的油炸面食充作无火之炊,那便是馓子最早的模样。苏东坡曾为其赋诗 “纤手搓成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亦赞其 “入口即碎,脆如凌雪”。千年流转,寒食的规仪早已淡去,但这缕酥脆却未曾断绝。它从历史的深巷里款款走出,带着古人的智慧与滋味,落进了济宁寻常百姓的灶台与心坎。
在济宁,馓子从不是寻常吃食,而是流淌在市井肌理里的生活印记。它看过运河帆影往来,听过老街坊的家长里短,陪着一代又一代人从垂髫小儿长成鬓角染霜的模样。传说济宁老字号王家撒子曾是清朝贡品,得乾隆御口亲封“馓子王”。故事虽无正史佐证,却藏着当地人对这门手艺的偏爱——能让寻常吃食与岁月传奇相连,那口酥脆里,早融进了匠心的厚重。目前,“王家馓子老店” 已传承四代,经过不断改良,形成独具济宁特色的细条馓子,以香、酥、细等特点闻名,成为本地以及周边地区家喻户晓的特色品牌。
如今走在济宁老街巷、农贸市场,仍能看到不少铺子支着油锅、揉着面团,缕缕油香伴着面香飘出巷口,勾着过往行人的食欲,也延续着这份刻在城市骨子里的味道。老辈人说,做馓子,本就是一场与时光的匠心相守。配料极简,不过面粉、盐、鸡蛋、清油,却应了那句大道至简——真味从不在繁复里藏着。老师傅的手是灵魂,揉面需至“三光”——面光、手光、盆光,那是力与柔的完美交融。晃条、缠股,细长的面丝在灵巧的指间如金线般穿梭、盘绕,最终投入滚烫的油锅。火候是无声的密语,多一分则焦,少一分则韧。唯有经验老到的匠人,才能让每一根馓丝都炸得通体金黄,薄如蝉翼,酥到极致,入口那声 “咔嚓” 轻响,像咬碎了初冬的阳光,满口香烈却毫无油滞,只留清醇在舌尖漫开——那一刻,运河的风、老街的暖,仿若都化在了这口酥脆里。
馓子在不少济宁人心中,是最惦记的味道。掰碎了撒在热腾腾的汤粥里,脆壳吸饱了汤的鲜,咬下去先是酥香,再是暖意漫到胃里——那是藏在记忆里幸福的味道;卷进刚出炉的烧饼或煎饼里,抹上点豆瓣酱,再夹根青辣椒,“咔嚓” 一声咬下去,辣椒的辣、酱的咸、烧饼的麦香,全被馓子的酥给串了起来。当岁末的炊烟裹着寒意漫过街巷,馓子便从寻常食盒跳进了年节的仪式里。不必说家家户户窗台那盘垒得像小山似的金黄,单是老人们念叨的 “金条拌生菜,来年发大财”,就把日子里的热望揉进了酥脆里。
在快节奏的今天,济宁的馓子铺依然坚守着那份传统。师傅们不追逐浮华,只专注于那一口锅、一双手、一份传承。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一口酥脆的馓子,就是打开乡愁的钥匙。那熟悉的味道,瞬间就能将人拉回运河畔的老屋,拉回母亲踮着脚从高处取下珍藏馓子的温暖午后,拉回围炉夜话、笑语喧哗的团圆时刻。它不是山珍海味,却比任何珍馐都更能抚慰人心,因为它承载的,是血脉里流淌的故土记忆,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是孔孟之乡在“食”这一最日常的维度上,对“礼”与“情”的无声诠释。
济宁的馓子,是运河水滋养出的金线,是时光窖藏出的味道。它用最朴素的食材,最繁复的手艺,最恒久的滋味,编织着这座城市最温暖、最坚韧的生活底色。当你在某个寻常日子,或是在年节的喧闹里,拈起一根金丝馓子,听它在齿间“咔嚓”绽开,那声音,便是千年运河边过日子的实在声,是手艺人传了一辈又一辈的真滋味,更是人间烟火里,最踏实、最绵长的幸福滋味。
这缕金丝,缠住了味蕾,也缠住了时光,更缠住了每一个济宁人心中最柔软、最不可替代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