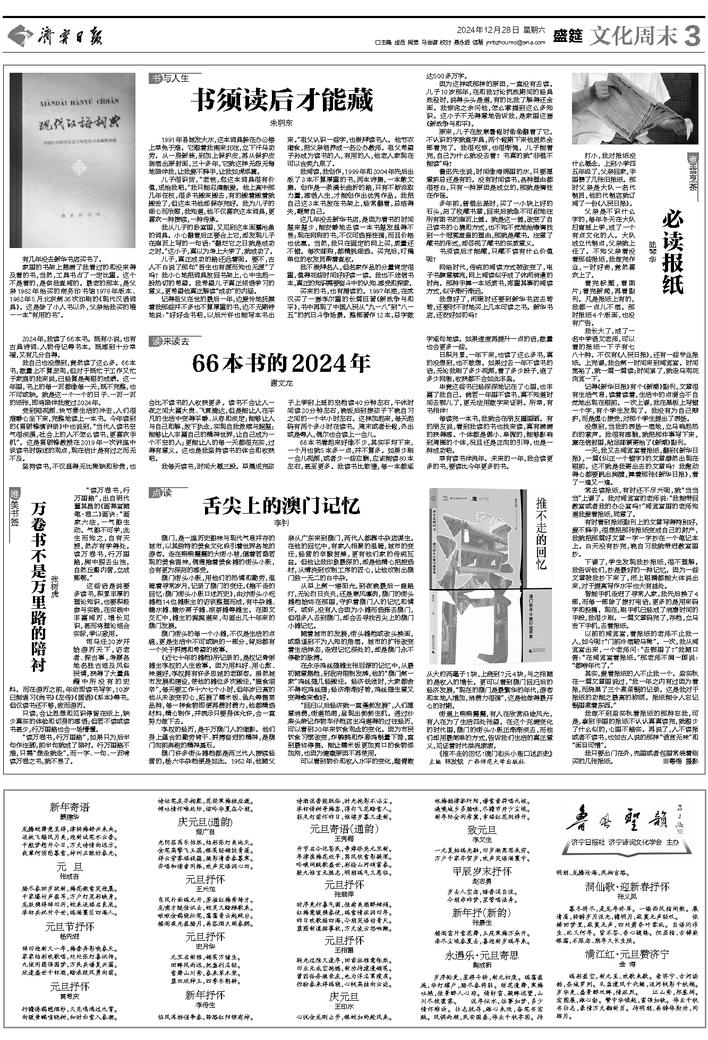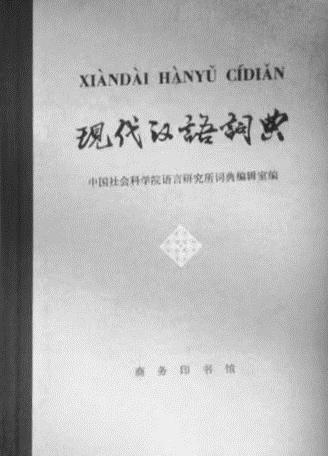有几年没去新华书店买书了。
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我看过的和没来得及看的书,当然,工具书占了一定比重。这个不是看的,是供我查阅的。最老的那本,是父亲1982年给买的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本、1982年5月北京第36次印刷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是除了小人书以外,父亲给我买的唯一一本“有用的书”。
1991年县城发大水,这本词典躲在办公楼上幸免于难。它跟着我南来北往,立下汗马功劳。从一身新装,到加上保护皮,再从保护皮剥落出原封面,三十多年,它就这样无怨无悔地陪伴我,让我爱不释手,让我如虎添翼。
儿子很识货,“老爸,您这本词典很有价值,送给我吧。”我只能忍痛割爱。他上高中那几年住校,很多书搬来搬去,有的搬着搬着就搬丢了,但这本书他却保存完好。我为儿子的细心而欣慰,我知道,他不仅喜欢这本词典,更喜欢一种接续,一种传承。
我从儿子的卧室里,又见到这本面露沧桑的词典。小心翻看后正要合上它,却发现儿子在扉页上写的一句话:“翻烂它之日就是成功之时。”这小子,真以为考上大学了,就成功了。
儿子,真正成功的路还远着呢。要不,古人不白说了那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了吗?我小心地把词典放回书架上,心中生起一股热切的希望。我希望儿子真正领悟学习的意义,更希望他真正解读“成功”的内涵。
记得祖父在世的最后一年,边爱怜地抚摸着我那些并不多也不算厚重的书,边不无期待地说:“好好念书吧,以后兴许也能写本书出来。”祖父认识一些字,也崇拜读书人。他节衣缩食,把父亲培养成一名公办教师。祖父希望子孙成为读书的人,有用的人,他老人家现在可以含笑九泉了。
我阅读,我创作,1999年和2004年先后出版了3本不算厚重的书,两本诗集,一本散文集。创作是一条漫长曲折的路,只有不断汲取力量,感悟人生,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我把自己这3本书放在书架上,经常翻看,总结得失,鞭策自己。
这几年没去新华书店,是因为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少,能安静地去读一本书越发显得不易;现在网购的书,不仅可选择性强,而且价格也优惠。当然,我只在固定的网上买,质量还不错。每次邮购,都精挑细选。买完后,叮嘱单位的收发员帮着查收。
我不崇拜名人,但名家作品的分量肯定很重,值得花些时间好好读一读。我也不迷信书本,真正的知识需要奋斗中的认知、感受和探索。
买来的书,也有漏读的。1997年底,在武汉买了一套李尔重的长篇巨著《新战争与和平》,书中再现了中国人民从“九一八”到“八一五”的抗日斗争场景。整部著作12本,总字数达500多万字。
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直没有去读。儿子10岁那年,在和我讨论抗战期间的经典战役时,说得头头是道,有的比我了解得还全面。我惊诧之余问他,怎么掌握到这么多知识。这小子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是家里这套《新战争与和平》。
原来,儿子在放寒暑假时偷偷翻看了它。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两个假期下来他居然全部看完了。我很吃惊,也很惭愧。儿子能看完,自己为什么就没去看?书真的就“非借不能读”吗?
鲁迅先生说,时间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没有时间读书,各种理由都很苍白,只有一种原因是成立的,那就是惰性在作怪。
多年前,曾借出差时,买了一小块上好的石头,刻了枚藏书章,回来后就急不可耐地往所有图书的扉页上盖。就是这一盖,改变了自己读书的心境和方式,也不知不觉地给懒惰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藏书。注意了藏书的形式,却忽视了藏书的实质意义。
书须读后才能藏,只藏不读有什么价值呢?
网络时代,传统的阅读方式被改变了,电子书肆意横流,网上阅读似乎成了休闲消遣的时尚。那种手捧一本纸质书,郑重其事的阅读方式,似乎渐行渐远。
我想好了,闲暇时还要到新华书店去转转,还要时不时地买上几本可读之书。新华书店,还安好如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