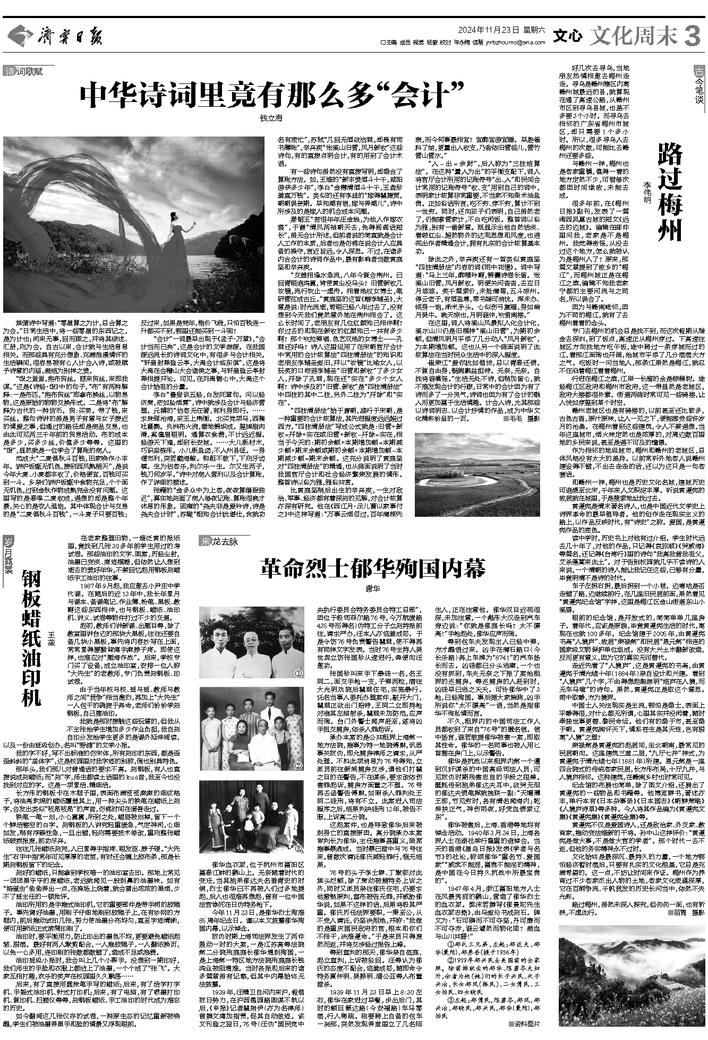好几次去寻乌,当地朋友热情相邀去梅州走走。寻乌是赣州辖区内离赣州城最远的县,就算现在通了高速公路,从赣州市区到寻乌县城,也差不多要3个小时。而寻乌去相邻的广东省梅州市城区,却只需要1个多小时。所以,很多寻乌人去梅州的次数,可能比去赣州还要多些。
与赣州一样,梅州也是客家重镇,值得一看的地方定然不少,可惜每次都因时间缘故,未能去成。
很多年前,在《梅州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湘西凤凰古城的短文《远去的边城》。编辑在邮件里问我,老家是不是梅州。我觉得奇怪,从没去过这个地方,怎么就被认为是梅州人了?原来,那篇文章提到了故乡的“梅江”,而梅州城正是在梅江之滨,编辑不知我老家宁都的主要河流与之同名,所以误会了。
因为与赣南毗邻,因为不同的梅江,就有了去梅州看看的念头。
专门去梅州的机会总是找不到,而这次假期从瑞金去深圳,到了饭点,高速正从梅州穿过。下高速往城区方向找地方吃午饭,途中跨过一条穿城而过的江,看那江面倒也开阔,给城市平添了几分落落大方之气。吃饭时一问当地人,那条江果然是梅江,就忍不住沿着梅江看看梅州。
行进在梅江之滨,江岸一长溜的全是棕榈树。途经梅江区政府和梅州市政府,这一带显然是老城区,政府大楼都很朴素。街道两侧时常可见一些骑楼,让人恍如穿越到某个时空。
赣州老城区也是有骑楼的,以前甚至还比较多,古色古香,原汁原味,让人一见之下,便能感受些许岁月的沧桑。在梅州看到这些建筑,令人不禁遥想,当年这座城市,烟火味定然也是浓厚的,对周边数百里地的乡民来说,甚至是遥不可及的憧憬。
作为相邻的地级城市,梅州和赣州的老城区,总体风格没有太大的差异。以前常听外地客人说赣州建设得不错,不出去走走的话,还以为这只是一句客套话。
和赣州一样,梅州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建城历史可追溯至北宋,千年来人文积淀丰厚。听说黄遵宪的故居就在城里,于是搜索地址找过去。
黄遵宪是清末著名诗人,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诗界革命的最早倡导者。他的创作走在现实主义的路上,以作品反映时代,有“诗史”之称。爱国,是黄遵宪作品的底色。
读中学时,历史书上对他有过介绍。学生时代远去几十年了,对他的作品,只记得《哀旅顺》《哭威海》等篇名,还记得《台湾行》里的诗句“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对于告别校园就几乎不读诗的人来说,一个清朝的诗人能让我记住这些,已够有分量,毕竟明清不是诗的时代。
车子左拐右拐,最后拐到一个小巷。边嘀咕是否走错了路,边继续前行,在几座旧民居前面,果然看见“黄遵宪纪念馆”字样,这里是梅江区金山街道东山小溪唇。
眼前的纪念馆,是开放式的,简简单单几座房子。看年代,应该是原貌,毕竟黄遵宪生活的时代,离现在也就100多年。纪念馆建于2005年,由黄遵宪书斋“人境庐”、故居“荣禄第”和民居“恩元第”相连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组成。没有大兴土木翻新改造,反而更有意义,因为它的真实无可替代。
走近先看了“人境庐”,这是黄遵宪的书斋,由黄遵宪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亲自设计和兴建。看到“人境庐”几个字,不由得想起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诗句。果然,黄遵宪正是取这个意思。闹中取静,方为境界。
中国士人关注现实是主流,哪怕是隐士,表面上平静得很,对什么都无所谓,心里其实并没闲着,随时牵挂世事更替、黎民命运。他们有的隐于市,甚至隐于朝。黄遵宪胸怀天下,情系苍生是其天性,岂有脱离“人境”之理?
荣禄第是黄遵宪的起居间,坐北朝南,最常见的民居朝向。这座建筑三堂二层,“九厅七井”样式,为黄遵宪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所建。恩元第是一座四合院式的传统客家民居,长方形布局,十厅九井,与人境庐相邻。这种建筑,在赣南乡村也时常可见。
纪念馆的布展也简单,除了图文介绍,还展出了黄遵宪的一些物品和书籍等。他博览群书,著述亦丰,单行本有《日本杂事录》《日本国志》《朝鲜策略》《人境庐诗草》等多种。今人将其作品编为《黄遵宪文集》《黄遵宪集》《黄遵宪全集》等。
黄遵宪不仅是爱国诗人,还是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推动变法维新的干将。孙中山这样评价:“黄遵宪是做大事,不是做大官的学者”。那个时代一去不返,但他的务实精神永不过时。
文化始终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一个地方哪怕经济暂时落后,只要有扎实的文化根基,它总是充满希望的。这一点,不妨让时间来作证。梅州作为养育过不少客家杰出人物的土地,客家文化底蕴深厚,它在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历史长河当中,依然不失光彩。
路过梅州,虽然未深入探究,但匆匆一面,也有斩获,不虚此行。■苗青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