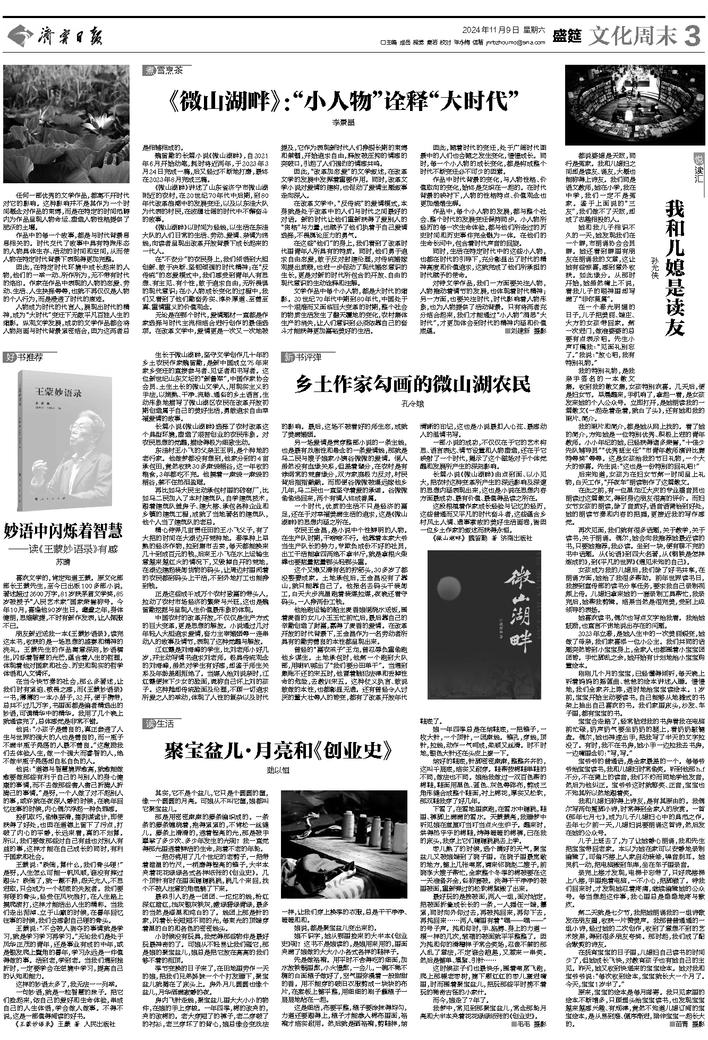其实,它不是个盆儿,它只是个圆圆的筐,像一个圆圆的月亮。可娘从不叫它筐,娘都叫它聚宝盆儿。
那是用密密麻麻的藤条编织成的。一条条的藤条缠绕着,抱得紧紧的,不肯松一丝缝儿。藤条上滑滑的,透着锃亮的光,那是被手摩挲了多少次、多少年发生的光呢?我一直觉得那光里透着鲜活的生命,刻着不老的年轮。
一把仿佛用了几个世纪的老剪子,一把带着暗星的竹尺,一柄磨得锃亮的锥子,大半本夹着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纸张的《创业史》。几个顶针有时在里面蹦蹦跳跳,跳几个来回,找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躺了下来。
最吸引人的是一团团、一坨坨的线,粉红深红暗红,浅灰银灰铁灰,嫩绿碧绿青绿,最多的当然是漆黑和纯白的了。线团上那是针的家,闪着长长短短不同的光,每束光的顶端穿着黑的白的和各色的密密线头。
小时候没有玩具,我觉得那些物件是最好玩最神奇的了。可娘从不轻易让我们碰它,那是娘的聚宝盆儿,娘总是把它放在高高的我们够不着的柜顶。
季节变换的日子来了,在田地里劳作一天的娘,把我们兄弟姊妹一个个打发睡下,聚宝盆儿就搁在了床头上。房外月儿圆圆也像个盆儿,月华洒满寂静的夜。
房内飞针走线,聚宝盆儿里大大小小的物件,在娘的手上穿梭。一年四季,棉的改夹的,夹的改棉的。老大穿短了的裤子,老二穿破了的衬衫,老三穿坏了的背心,娘总像会变戏法一样,让我们穿上换季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暖暖和和。
娘说,都是聚宝盆儿变出来的。
娘不识字,她从哪里捡来的大半本《创业史》呢?这书不是娘读的,是娘用来用的,里面夹满了娘做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鞋样子。
先是做袼褙。用平时不舍得吃的细面,加水放铁锅里熬,小火慢熬,一会儿,一碗不稀不稠的白面糨子做好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甜甜的香。用不能穿的破旧衣服剪成一块块的布片,在案板上铺平整,用细细的刷子蘸糨子一层层地粘在一起。
这是细活,布要平整,糨子要涂抹得均匀,力道还要跟得上,糨子才能渗入棉布里面,袼褙才结实耐用。然后就是晒袼褙,剪鞋样,纳鞋底了。
娘一年四季总是在纳鞋底,一把锥子,一枚大针,一个顶针,一团麻线。锥孔,穿线,顶针,拉线,动作一气呵成,柔顺又丝滑。时不时地,银色大针还在头皮上撩一下。
纳好的鞋底,针脚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这叫千层底,结实又耐穿。鞋帮按棉鞋单鞋的不同,做法也不同。娘给我做过一双百色帮的棉鞋,鞋面用黑色、蓝色、灰色等碎布,剪成三角形缝合成整个鞋面,衬上棉花,厚实又松软,那双鞋我穿了好几年。
下雪了,在雪地里疯跑,在雪水中蹦跳,鞋里、裤脚上满满的雪水。天蒙蒙亮,我睡梦中听见娘在堂屋叮当叮当点火生炉子。醒来时,烘得热乎乎的棉鞋,烤得暖暖的棉裤,已在我的床头,我穿上它们蹦蹦跳跳去上学。
枣儿熟了的时候,选个晴好的天气,聚宝盆儿又被娘端到了院子里。在院子里最宽敞的地方,铺上几张苇席,请来邻院赵二嫂子,前院李大嫂子帮忙,全家整个冬季的棉被要在这一天准备齐全,俗称套被。洗得干干净净的被里被面,重新弹过的松软棉絮搬了出来。
最好玩的是拽被面,两人一组,面对站定,把被面折叠成长长的一条,一人握住一端,攥紧,同时向外仰过去,再被扽回来,再仰下去,再扽回来……两人嘴里有着“嘿——嘿——”的号子声。扽和仰时,手、胳膊、身上的力道一模一样的几次,皱褶的被面就平平整整了。因为扽和仰的滑稽样子常会笑场,忍俊不禁的那人乱了章法,不定谁会趔趄,又惹来一串笑。然后是铺单、填絮、引针……
这时候孩子们也最快乐,围着苇席飞跑,爬上那棵老枣树,摘下颗红红的枣儿塞进嘴里,时而围着聚宝盆儿,把玩那些平时捞不着玩的稀奇古怪的小家什。
而今,娘走了7年了。
我梦中,常见到那聚宝盆儿,常念那轮月亮和大半本夹着花花绿绿纸张的《创业史》。
■毛毛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