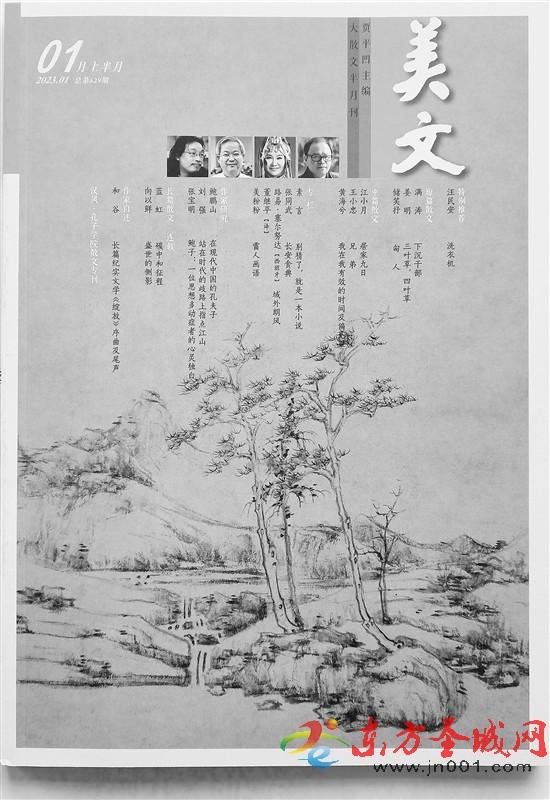刊发于《美文》杂志2023年01期的短篇散文《下沉干部》,写出了下沉干部深入社区参与24小时全封闭疫情值守,大半个月不能回家,不便洗澡,搭帐篷、睡地铺,与物业、社区人员和居民朝夕相处的故事。
其间交织着送儿子出国,帮居民找狗等叙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作者满涛,既是一名作家,又是资深媒体人,双重学养的浸润,让他建构出《下沉干部》这样一篇短小精悍,又寓意丰富的散文。
在如今这段阅读时光,新闻与文学的分野日渐模糊。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也曾试图对新闻和文学进行区分,他得到的结论是:文学的内容大于新闻。
我们读新闻,意味着对其完全消费,如人物、时间、事件、结果,一清二白;而文学的概念明显更加宽泛,存在某种不可被消耗的内核。至于这种内核到底是什么,本雅明语焉不详。
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更加难以找到答案。如今的新闻写作几乎吸收了所有文学创作的特点,新闻人在副刊等阵地创作出高度文学化的作品,引人入胜;与此同时,小说和散文作家也借鉴非虚构的写作视角,对虚构的情节进行弱化。这就造成了一种内容的同质化。
作为媒体人的作家满涛,散文写作的视角跳出了这种新闻与文学风格之间的纠葛。
《下沉干部》的写作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读后或许会让熟悉作者本人和其职业的读者会心一笑,这一特点就是他对自己文本写作的解读。
如“有人送来满满一大盆羊肉豆腐犒劳我们(都被老李端走了)”“幸好准备充分(保证书、录取通知等)”“过了两天,张经理又做了拿手的葱油‘瓜搭’(类似油饼)”等,括号内的文字,充当了前文的注脚,是作者本人对文字的解读,亦是一种补充和娓娓道来式的评说。
实际上,在中国古典世情小说中,评论家和作者间的互动十分常见,甚至密不可分。如《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有脂砚斋批语近三千条,平均每回有四十条之多,而这些批语大致可以为三类:一是对曹雪芹生平和家世背景的介绍,二是对文本情节的引申解读,三就是对后文情节的透露。
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一定不会错过脂砚斋的批语,其中的“剧透”,是对写作者创作的巨大补充。而据说曹雪芹本人,同样因为脂砚斋的建议,修改了大量文字。
这种“共生”关系,默契十足,也证明了评论家评说的重要性。满涛在文本创作的过程中,一个人担当起了作者和评论家两个角色,以独立的评说对文本进行解读,这是《下沉干部》带给我们的一大惊喜。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短篇散文中的纪实性。文学的“非虚构”,在广义上仍允许有部分虚构内容,因为作者往往不是当事人,在采访、采风过程中的口授亦或被采访者的口口相传,理论上存在着叙事上的空缺和中断,这就必然导致了文本作者的虚构和想象。
满涛作为下沉社区参与工作的当事人,在写作时刻意保留了大量亲身经历的内容,这种文体其实介于新闻与“非虚构”的文学创作之间,比广义上的“非虚构”更加真实,比传统的新闻写作,则是多了更多叙事和想象。
散文是小而精的题材,大多数散文和短篇小说是美的,从中国的古典文本一直延续至今。更准确地说,即便结局不甚完美,散文和短篇小说作者,往往也会用另一种代偿机制,来对文本的叙事进行弥补。
如家喻户晓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然是爱情悲剧故事,但在文章最后,仍有一对从坟墓中飞出的蝴蝶。这一对蝴蝶,正是作者对现实无奈的补偿性虚构。看到蝴蝶破茧而出,我们会认为这对苦命情侣最终成双成对了,心里也会得到一丝安慰。
来到近现代,这种代偿机制逐渐消失,文本作者开始关注生命个体,在写作时往往少了这种补偿性虚构,更加注重和呈现现实。
在《下沉干部》中,作者写“隔壁小区不时传来危情,眼看着大白和大巴车连续两天将人带走隔离。起因是一个居民在小区里摆摊卖菜,结果本人是阳性,导致整个小区成为高风险区。受此影响,我们小区刚红火了三天的小超市又关门了”。
或许在读者眼中,这种真实的场景不够“美”,但在笔者看来,满涛的叙事真实而凌冽,有直达内心的力量,这不失为一种独特的美丽。换句话说,真实的叙事有时候也很浪漫,这是满涛作为新闻人的浪漫,更是满涛作为作家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