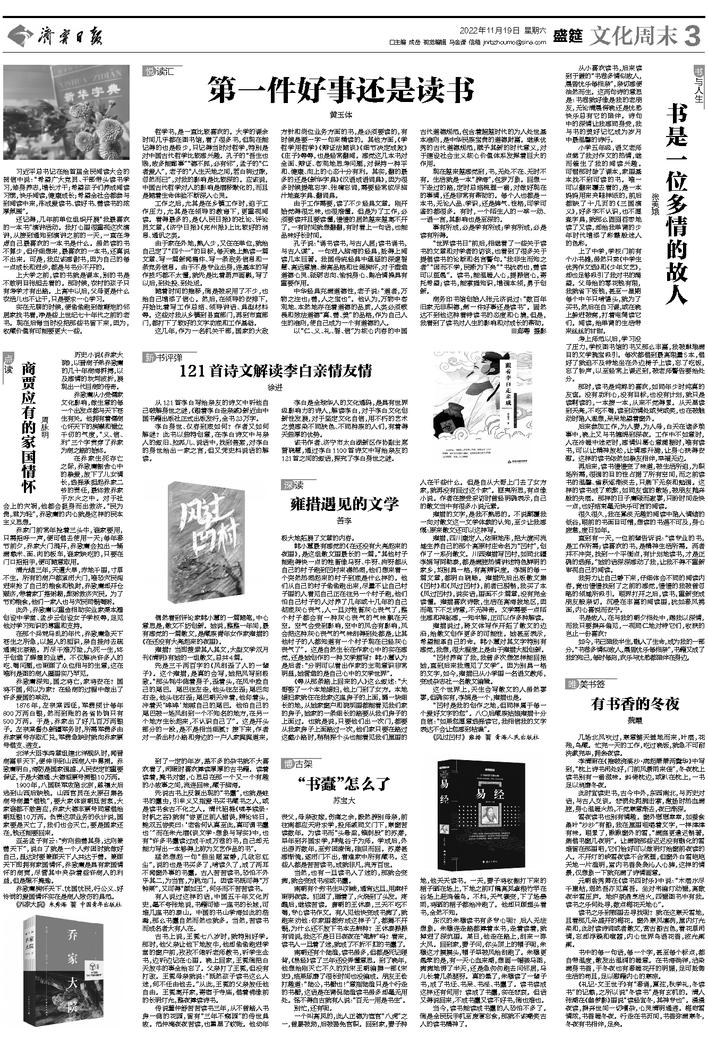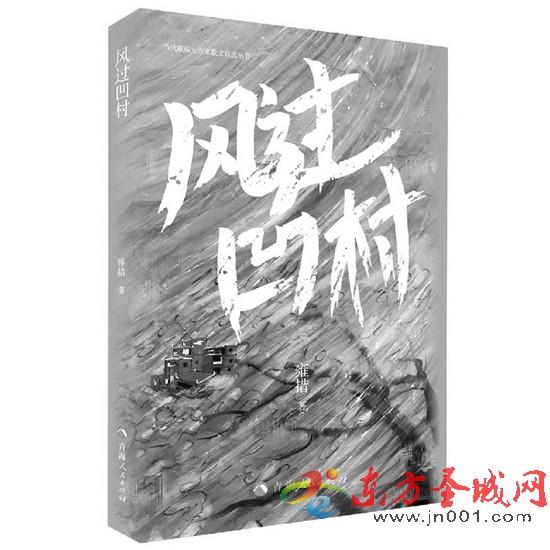偶然看到评论家韩小蕙的一篇随笔,中心意思是,散文不妨创新。她说,整整一年间,最有感觉的一篇散文,是藏族青年女作家雍措的《在还没有大亮起来的夜里》。
雍措?当即搜索其人其文,大型文学双月刊《清明》有她的一组散文,总共4篇。
先是三千两百字的《风刮歪了人的一辈子》。这个雍措,是真的会写,她把风写到极致。“那头牦牛侧着身子,歪着头,在风中捡自己的尾巴。尾巴往左走,他头往左歪;尾巴向右走,他头往右歪;尾巴朝天冲着,他仰着头,冲着天‘哞哞’地喊自己的尾巴。他怕自己的尾巴被一场风刮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在另一个地方生长起来,不认识自己了”。这是开头部分的一段,是不是相当细腻?接下来,作者对一条出村小路和旁边的一户人家娓娓道来,极大地拓展了文章的内容。
韩小蕙最有感觉的《在还没有大亮起来的夜里》,是这组散文里最长的一篇。“其他村子能跑得快一点的牲畜像马呀、牛呀、狗呀都从自己的村子跑到凹村来凑热闹,他们想来看一个突然热闹起来的村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从自己的村子偷偷跑出来,尽量不让自己村子里的人看见自己正在往另一个村子跑,他们怕自己村子的人对养了几年或十几年的自己彻底灰心丧气,人一旦对牲畜灰心丧气了,整个村子都会有一种灰心丧气的气味飘在天空。空气会受到影响,空中的风会有影响,风会把这种灰心丧气的气味刮得到处都是,让其他村子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村子现在已经灰心丧气了”。这是自然生长在作家心中的实在感觉,还是她创作的一种文学描写?韩小蕙认为是后者:“分明可以看出作家的主观意识非常明显,她营造的是自己心中的文学世界”。
《等从那条路上回来的人》这么叙述:“大哥娶了一个本地媳妇,他上门到了女方。本地媳妇家就住在我家这座房子的上面,隔一块细长的地,从她家窗户和院坝里都能看见我们家的房子,她家的一条细长的路要从我们房子的上面过。也就是说,只要他们出一次门,都要从我家房子上面路过一次,他们家只要在路过这截小路时,稍稍探个头也能看见我们屋里的人在干些什么。但是自从大哥上门去了女方家,就再没有回过这个家”。匪夷所思,有点像小说。作者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明确表示,自己的散文当中有很多小说元素。
雍措的文字,是我不熟悉的。不说颠覆我一向对散文这一文学体裁的认知,至少让我感慨:原来散文还可以这样写。
雍措,四川康定人,依照地形,把大渡河流域生养自己的那个高原村庄命名为“凹村”,创作了一系列散文。川西雍措写凹村,如同北疆李娟写阿勒泰,都是满腔热情讲述特色鲜明的家乡,均别具一格,有高辨识度。李娟的每一篇文章,都明白晓畅。雍措先后出版散文集《凹村》和《风过凹村》,前者已脱销,我买了本《风过凹村》,说实话,里面不少篇章,没有完全读懂。雍措喜欢诗歌,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因而笔下不乏诗意,不无神奇。文学需要一点陌生感和神秘感,一知半解,正可以作多种解读。
雍措说过,跨文体写作开拓了散文的边沿,给散文创作更多的可能性。她甚至表示,希望能革自己的命。韩小蕙对其文字特别有感觉,我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雍措大胆创新。
“凹村养育了我,我曾多次想怎样能回报她,直到后来我遇见了文学”。因为别具一格的文字,如今,雍措已从小学里一名语文教师,变成杂志社一名散文编辑。
这个世界上,天生会写散文的人虽然寥寥,但确实有,李娟是一个,雍措也是。
“凹村是我的创作之地,但同样属于每一个爱好文字的您”。八〇后藏族姑娘雍措十分自信:“如果您愿意选择读它,我相信我的文字表达不会让您感到枯燥”。
《风过凹村》 雍措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