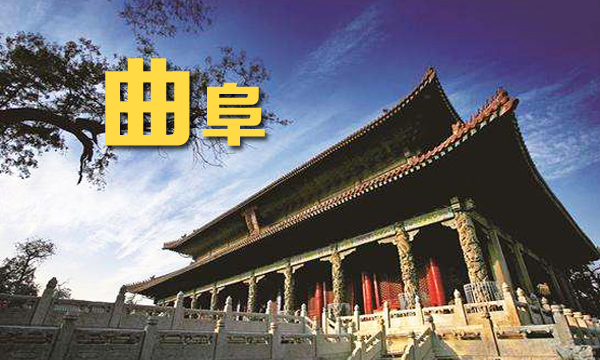圣乡食事丨鱼香沉锚:百年滋味里的济宁心跳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娜
济宁的晨光,总带着古运河的潮气。当竹竿巷的青石板还凝着露水时,那口熬了六代晨昏的鱼锅已在灶台上温着,咕嘟着缠在记忆里的酸香,像一根无形的线,一头拴着19世纪末运河码头的帆影,一头牵着此刻推门而入的街坊。
百年前的林家湾,是运河留给济宁的一隅盛着烟火的港湾。码头工人们卸下纤绳,汗水还挂在黝黑的脊梁上,便循着那口锅的热气围拢过来。杨续文掀开木盖的刹那,微山湖的鱼香裹着白雾漫上来,骨酥入味的熨帖,正顺着热汤漫进他们紧绷的筋骨里。“推车的、挑担的,无人不吃林家湾鱼”——民谣里的热闹,是码头边最鲜活的人间,那些被鱼肉暖透的胃,第二天又能扛起运河上的风浪。
如今旧巷虽已不在,竹竿巷的店里,时光依旧在鱼香里静静流淌。清晨六点,微山湖的渔民准时送来活蹦乱跳的野生小草鱼,近百斤的鲜鱼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完毕——这是林家六代人雷打不动的规矩。杀鱼、洗净、入冰柜,动作行云流水;待到下午,这些鱼便要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滚油中炸至金黄酥脆,晾置一夜,待第二日清晨与秘制香料相遇。
这口老味里,藏着运河滋味的百年密码。最早用的是微山湖特有的“鲹子鱼”,细长骨软,鱼肉自带甘甜。后来运河变迁,鲹子鱼难觅踪影,只得改用草鱼鲫鱼,老食客至今仍念叨“草鱼不及鲹子香酥”。但杨家人自有应对之法:腌渍一段时间的鱼先用急火炸透,慢火炖至骨酥,最后再用小锅焖上。老汤则以十余种香料分时段入锅,配方随节气微调,配上恰到好处的火候,既保留当年码头工人最爱的辛香底色,又添了令现代食客惊艳的回甘。
掌勺人搭在锅沿的手,掌心里焐着的,正是对百年工艺较真的温度。当棕红浓汤里浮起七八条金黄小鱼,撒上翠绿葱花时,那“骨酥肉嫩不扎嘴,汤浓饼香鱼在游”的滋味,便成了穿越时空的味觉契约——如今的竹竿巷里,炸鱼的油花还在飞溅,恍惚间与百年前码头支锅的烟火重叠在一起。
端上桌的炖鱼,像时光沉淀的滋味。红汤里的小鱼裹着浓稠的汤汁,葱花点缀其间,恍若运河水面的细碎波光。筷子轻轻一夹,鱼肉便顺着纹理绽开,酸香先在舌尖漫开,接着是鱼肉的鲜嫩、鱼骨的酥软,热汤下肚,浑身都透着舒坦。老济宁人总爱把油饼撕成小块,让麦香吸饱鱼香——这一口,藏着奶奶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父亲收工后的踏实满足,孩童趴在桌边急不可耐的馋样,一辈辈的寻常日子,都浸在这口味道里。
店里的食客总带着故事。老街坊张大爷每周三必来,他说这味道和小时候趴在爷爷肩头闻到的一模一样,那时运河上的船还吐着白汽,偶尔夹着几缕青烟;年轻情侣从上海赶来,女孩舀着汤笑,说这是济宁给她的第一份温柔;步履匆匆的上班族边回邮件边喝汤,手机屏幕倒映着汤面涟漪;穿校服的少年狼吞虎咽,他不知道,自己此刻咂嘴的模样,和百年前码头边那个蹭鱼吃的孩童,如出一辙。
林家湾炖鱼早已不只是一道菜了。它是运河写给济宁的绵长情书,字里行间都是烟火气的深情。当城市的高楼遮住了昔日帆影,这缕倔强的酸香,便如一枚沉锚,让漂泊者不忘来路,让归家的人暖意满怀。六代人的守护,炖的何止是鱼?何尝不是一座城的念想……只要灶火不熄,济宁的故事,就永远咕嘟着醇厚的滋味。
 登录
登录
 数字报
数字报 旧版入口
旧版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