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缸里的光阴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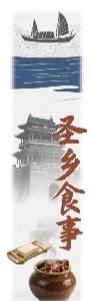

开栏的话
食之大者,养身亦养心!
当甏肉干饭的浓香漫过运河古岸,当托板豆腐的叫卖声穿透太白楼晨雾,一箸一肴间,一座城的千年文脉便有了温度。昔年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箴言,滋养出这方水土对滋味的无限虔诚;南来北往的漕船千帆过处,终将八方风味沉淀为济宁的包容之魂。
即日起,本栏循着《论语》的余韵、运河的桨声,带您品读《圣乡食事》——
以舌尖丈量儒家饮食美学的深度,
用故事打捞沉浮市井的味觉记忆,
在千年圣城的袅袅炊烟里,
照见中国人最温热的生存智慧与生命欢愉。
一城食事待君尝,半是风雅半是禅。
掌上济宁讯(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娜)运河的晨雾漫过济宁城时,玉堂酱园的晒场总先醒。三千口酱缸静蹲在朝阳里,缸沿浸着晨光,像一圈圈凝固的涟漪。竹编缸盖揭开的刹那,醇厚的酱香便漫过青石板路,混着运河的水汽,在老济宁人的鼻尖缠缠绕绕,一绕就是三百多年。
老辈人说,玉堂的酱菜是有灵性的。康熙年间那个苏州船户戴氏,带着江南的甜脆闯进北方的咸鲜里,在酱缸前反复琢磨。他的手抚过腌透的萝卜,指尖能辨出盐分渗入的深浅;耳朵贴着缸壁,能听出酱坯发酵的细微声响。当第一坛融合了南北滋味的什锦菜出缸时,运河码头的纤夫们捧着粗瓷碗,嚼出了他乡遇故知的暖。
这些酱缸最懂光阴的重量。三伏天正午,匠人古铜色的脊背沁着汗珠,手中的木耙起落如钟摆,让每片菜蔬都饱蘸阳光;数九寒冬,又为酱缸披上棉衾,任微生物在黑暗里酝酿。堂前“味压江南”的金匾虽耀眼,却不及缸沿深浅不一的纹路更懂匠心——那是三百年来无数掌纹的叠加,是岁月包浆里渗出的琥珀光,每一道都刻着“慢慢来”的笃定。
济宁人的日子,总裹着玉堂的酱香。北门里张奶奶的回忆里,六十多年前运河结冰那阵,父亲踩着雪走了三里地,攥着皱巴巴的粮票换回来半瓶酱黄瓜。兄妹三个围着粗瓷碗,就着稀粥把碗底舔得发亮,那点咸香成了寒冬里最扎实的盼头。后来她嫁人的陪嫁里,压箱底的除了棉被,还有个贴红喜字的玉堂酱菜坛,“日子再紧巴,坛里有酱菜,心里就不慌”。
这份“不慌”,跟着济宁人走南闯北。离家多年的李奶奶总说:“我家橱柜永远留着一格给玉堂。”清晨熬粥时,捏一根酱黄瓜切碎了拌进去,米香里立刻浮起清冽的咸鲜;端午包粽子,蜜枣馅里要掺些酱姜芽,甜糯中藏着一丝微辣的醒神;就连过年的饺子,蘸料里少了那勺玉堂甜面酱,孩子们都要噘起嘴。“这味道太熟了,熟到像母亲的唠叨,平时不觉得特别,可离家久了,却成了舌尖最执拗的念想。”
去年腊月,有位回乡过年的年轻人,在酱菜柜台前站了许久。他指着玻璃罐里的酱花生,声音发颤:“就这个,我妈以前总爱装在我背包里。”售货员笑着递过罐子,年轻人拧开盖子的手都带着急,捏起一颗塞进嘴里——眼眶忽然就红了。这哪里是一颗酱花生呢?是远行时母亲掀开背包拉链的轻响,是车站安检时隔着塑料袋传来的微咸,是无数个异乡深夜里,想起济宁城慢悠悠晨昏时,舌尖泛起的那点熨帖。
如今,运河边的老店还在,“玉堂”二字被风雨浸得温润。常看见白发老人拄杖而来,买上几样酱菜,揣在怀里慢慢走,像揣着一捧旧时光。也有年轻人对着玻璃柜细细挑选,不时与身旁人絮语:“还得是玉堂酱莴苣,咬着有筋骨,脆生生的劲儿藏不住”“就像小时候姥姥接我放学,布兜里总摸出半块,咸津津的香一漫,心里早开了花”……玻璃罐里的酱瓜泛着琥珀光,入口先是咸鲜在舌尖炸开,尾调却缠上一缕江南的甜,像极了运河水——早把南北的滋味融在了一处,淌进了寻常人家的烟火里,也淌进了一辈辈人的心窝里。
这便是玉堂的味道,藏在老酱缸的光阴滋味里,也浸在济宁人的日子里。这滋味里藏着济宁城的魂。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文物,不是旅游手册上的风景,而是舌尖上那点挥之不去的咸鲜,是岁月泡不淡的念想。是张奶奶陪嫁坛底压着的踏实,是李奶奶橱柜里守着的念想,是年轻人背包里捂热的牵挂,更是三百年间,济宁人对日子最朴素的热望。
运河的水昼夜不息地淌,酱缸里的故事仍在发酵。那些藏在咸香里的光阴,那些融在脆嫩中的坚守,早成了济宁人血脉里的味觉记忆。一碟玉堂酱菜摆在桌,筷子夹起的不只是菜,是三百年的日月星辰,是运河码头的号子,是灶台上的烟火,是祖祖辈辈嚼进岁月里的——暖。
 登录
登录
 数字报
数字报 旧版入口
旧版入口


